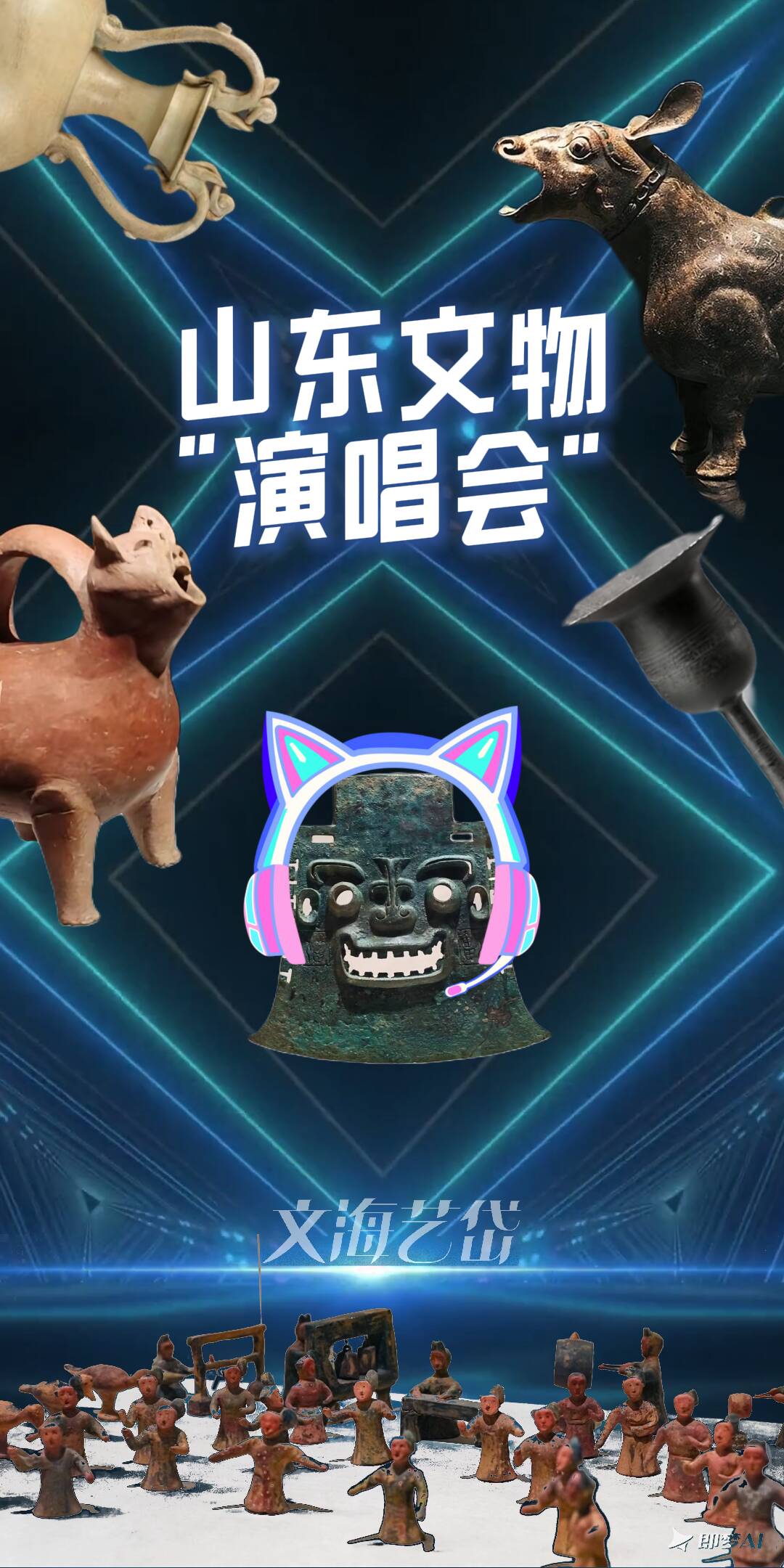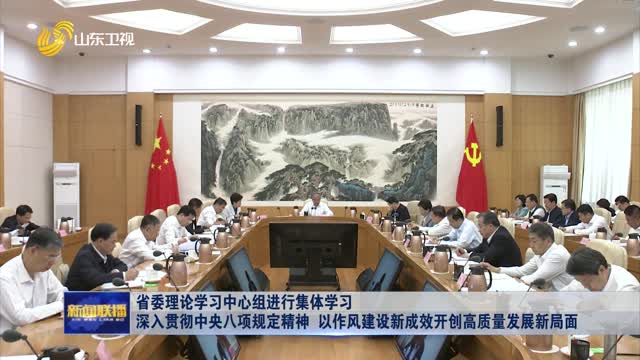探索構建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第三方主體封存義務制度
來源:檢察日報
2025-05-19 08:53:05
原標題:探索構建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第三方主體封存義務制度
來源:檢察日報
原標題:探索構建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第三方主體封存義務制度
來源:檢察日報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這是應對我國犯罪結構發生顯著變化所作出的頂層設計。筆者認為,在系統總結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立法與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應專門關注科學技術更新迭代與廣泛應用,特別是犯罪記錄信息數字化對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構建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在此,筆者擬探討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第三方主體的封存義務。
犯罪記錄數據化現象應予以重視
數字化技術已滲透至人類社會活動的各方面,數據信息、算法和平臺的重要性愈加凸顯。在刑事司法數字化改革趨于深入的背景下,海量的犯罪記錄已不再僅以紙質形態存在,而是廣泛存儲于網絡空間,由此催生犯罪附隨后果數字化現象。這種因應技術和算法運行而生成的犯罪記錄數據,應成為構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重點關注對象。
一方面,犯罪記錄數據的持有主體呈現多元性特征。其一,圍繞數字檢察、數字警務、數字法院建設而開展的各類改革方案和措施更新,使得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工作中形成大量數據化信息。這些數據信息的表現形態之一即海量的犯罪記錄數據。通常情況下,公權力機關是主要的犯罪記錄數據持有主體。其二,以網絡服務者、技術服務者為代表的主體提供技術支持和其他輔助服務,從而與政府、司法機關的合作愈加緊密。在此過程中,網絡服務者、技術服務者會獲得相當體量的犯罪記錄及其相關數據。除此以外,為了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滿足市場需求,網絡服務者、技術服務者還會通過各種技術手段與算法收集網絡中的犯罪記錄信息,形成包括犯罪記錄數據在內的數據庫,為其客戶提供查詢等服務。其三,當前網絡技術發達,以形式多樣的應用程序為代表的平臺和軟件在幫助用戶提高信息獲得速度的同時,也無形中承載了大量不容忽視的違法犯罪記錄數據碎片。這些數據碎片體量龐大且易被迅速傳播。下載、擴散這些犯罪記錄數據的主體通常是使用自媒體軟件的用戶。其四,基于工作需要,新聞媒體、科研機構也會通過多種方式獲得犯罪記錄數據并用于新聞報道和研究等活動。可見,亟須研究國家公權力機關和犯罪行為人以外的第三方主體對犯罪記錄數據的封存義務。
另一方面,傳統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尚存在主體類型偏少、封存范圍狹窄等有待進一步完善之處。客觀而言,現有的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尚不足以應對犯罪記錄數據化所帶來的問題。其一,針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封存義務主體主要是國家公權力機關。基本上沒有專門關照犯罪記錄數據持有第三方主體特別是網絡服務者和技術服務者的封存責任。這可能增加犯罪記錄數據不當擴散的風險。而且,現有規定要求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分別負責職權范圍內的封存和查詢工作,也容易引發各職能部門對于犯罪記錄數據封存工作溝通不暢的后果。其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范圍主要包括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全部案卷材料,較少涉及網絡服務提供者等第三方主體所持有的犯罪記錄數據和相關信息。即使有關文件要求國家公權力機關封存電子檔案信息,此類規定也遠不足以涵蓋第三方主體借助技術和算法篩選、匯總、整理和加工而形成的犯罪記錄數據。
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第三方主體封存義務的若干面向
構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不能照搬既有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方案,而應順時順勢,構建針對犯罪記錄數據封存的專門體系,重點健全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第三方主體的封存責任機制。換言之,數字化時代倘若犯罪記錄封存規范沒有涵射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第三方主體,那么立法所期待的封存犯罪記錄目標和效果恐難實現。
第一,結合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不同主體,明確犯罪記錄數據類型。廣義上的犯罪記錄數據可被理解為存儲于網絡虛擬空間的記載犯罪信息的各類數據信息。若以此為標準界定待封存的犯罪記錄數據的范圍,不僅會帶來繁重的執法司法成本,而且會影響公眾知情權和新聞自由。為此,對于成年人涉嫌輕微犯罪且需要封存的犯罪記錄數據,需要結合數據持有主體來確定相應的犯罪記錄數據類型。這些由第三方持有的犯罪記錄數據包括但不限于:一是網絡服務者、技術服務者通過購買、抓取、合作等方式獲得的犯罪記錄數據;二是新聞媒體、科研機構獲取的犯罪記錄數據;三是網絡用戶個體持有的犯罪記錄數據。就第三方主體持有的犯罪記錄數據而言,應重點關注第一種和第三種犯罪記錄數據封存的必要性。
第二,科學界定持有犯罪記錄數據且承擔封存義務的第三方主體范圍。強調第三方主體的封存義務,絕不意味著只要持有犯罪記錄數據便承擔封存責任。基于犯罪記錄數據收集、傳播與售賣而形成商業模式的網絡服務者、技術服務者擁有相對主導的地位,此類第三方主體既有突出的技術與算法優勢,又能夠建立并運行記載海量信息的數據庫,理應承擔相應的封存義務。此外,因各種原因持有本應封存的犯罪記錄數據的網絡用戶也應注意控制傳播范圍,避免侵犯相關人員的合法權益。考慮到公眾知情、輿論監督的現實需要,應慎重要求新聞媒體承擔犯罪記錄數據封存義務,這種區分思路反映了犯罪記錄封存價值與其他價值的平衡。
第三,辨明承擔犯罪記錄數據封存義務的第三方主體的主要責任。對于國家公權力機關發布封存指令的案件,包括網絡服務者、技術服務者在內的第三方主體應當禁止披露、傳播或者使用相應的犯罪記錄數據。同時,這些第三方主體還應承擔定期更新犯罪記錄數據庫的責任。對于已被要求封存的犯罪記錄數據,為了避免相關主體濫用數據,可要求第三方主體刪除有關數據。特別是,如若第三方主體通過與國家公權力機關合作的方式獲得犯罪記錄數據,國家公權力機關應在合作協議中明確犯罪記錄數據保管、刪除等義務,并設置相應的責任規則。總體上,從市場經濟角度看前述第三方主體的封存義務和責任,更需要明確行政執法機關承擔的履職要求,以及確立第三方主體承擔的行政處罰和其他責任。
第四,完善犯罪行為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權益保障與救濟機制。對于第三方主體未能履行封存義務而導致犯罪記錄數據不當擴散后果的情況,一方面,應允許利害關系人通過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獲得救濟,另一方面,也可在個人信息保護法賦予刪除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確立被遺忘權的本土化路徑。
第五,檢察機關協同探索犯罪記錄數據管理與封存制度。檢察機關在對國家公權力機關的犯罪記錄封存工作進行法律監督的同時,要順應犯罪記錄數據封存的發展趨向,與其他公權力機關協同探索犯罪記錄數據集中統一管理、更新與封存的可能前景。在此領域,檢察機關也可探索引入人工智能進行犯罪記錄數據識別、篩選與封存活動,建立專門針對持有犯罪記錄數據的第三方主體的封存模型與監督制約模型,并不斷進行迭代升級,從而適應新時代技術革新對刑事司法活動運行規律的要求。
[作者為山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基礎理論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檢察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護航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
- 本報訊近日,陜西省教育廳組織28所省內高校赴山東濟南開展聯合訪企拓崗暨校企對接促就業活動。累計組織各類招聘活動8926場,發布崗位信息28...[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5-19
每顆種子都釋放出生命的氣息
- “黑芝麻白扁豆,紫蘇黃連與青蒿,小茴香大青葉,半夏三七加八角……”在山東省臨沂第十中學,每天陽光大課間,小學部響徹校園的《本草歌》...[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5-19
作文課上的一場“意外”
- 在我多年的教學經歷中,有一堂課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是一節初中語文的作文課,按照計劃,這堂課要講解記敘文寫作中的細節描寫技巧。學生們聽...[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5-19
構建育人“教聯體” 共繪成長“同心圓”
- 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泉欣小學以學生成長為核心,構建“泉欣·大家”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聚合各方力量形成育人合力,挖掘拓寬差異化教...[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5-19
立足新文科建設 培養地方特色人才
- 臨沂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立足沂蒙,面向山東,輻射全國,主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掌握文物學、博物館學的基本知識和理論,熟悉文物...[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5-19
那些溫暖動人的少審故事,一起匯聚而成法治的光!
- 本報訊“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辦的往往不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這個案件首次認定,對于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的違法侵權信息,網絡平臺應當...[詳細]
- 人民法院報 2025-05-18
外貿產品轉內銷提速增量
- ??為應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助力外貿企業穩住市場份額、降低運營成本,各地正在積極施策,幫助外貿企業不斷拓寬內銷空間,內外貿一...[詳細]
- 新華網山東頻道 2025-05-18
技術驅動 機制保障 法治引領
- ■點評近年來,各地公安機關堅持創新驅動,以新警務理念為先導、以新運行模式為關鍵、以新技術裝備為支撐、以新管理體系為保障,提升公安機...[詳細]
- 人民公安報 2025-05-18
數智解碼平安 守護更有溫度
- □本報記者孫麗麗通訊員李冰峰原誠鹍在失聯人員查找工作中,全警一體化運轉,找回成功率達98.7%;在打擊盜竊專項行動中,數據匯集碰撞,精...[詳細]
- 人民公安報 2025-05-18
子彈庫帛書《五行令》《攻守占》回家
- 本報北京5月17日電記者李韻17日從國家文物局獲悉,漂泊美國79載的子彈庫帛書《五行令》《攻守占》終于回歸祖國。??子彈庫帛書是目前出土...[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5-18
黃渤海海霧綜合觀測研究及人工消霧科學試驗開展
- 本報北京5月17日電記者崔興毅從中國氣象局獲悉,今年首次黃渤海海霧綜合觀測研究及人工消霧科學試驗日前在山東青島拉開帷幕。本次研究及試...[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5-18
持續升溫!入境游熱潮涌動
- 在景德鎮,體驗瓷器制作的外國游客化身“手藝人”,耐心地拉坯、彩繪。“免簽政策太方便了,這是我第三次坐郵輪到中國,之前去了上海、廣州...[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