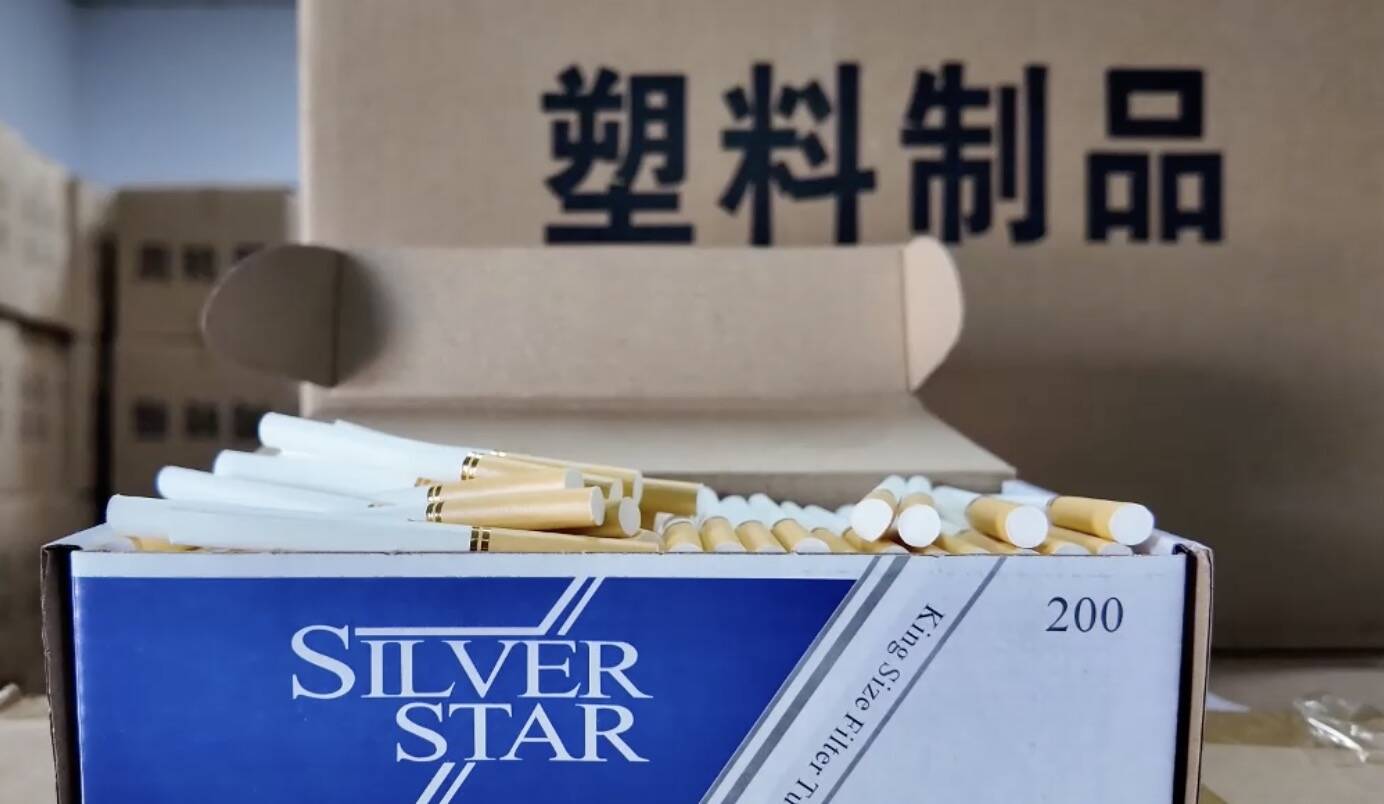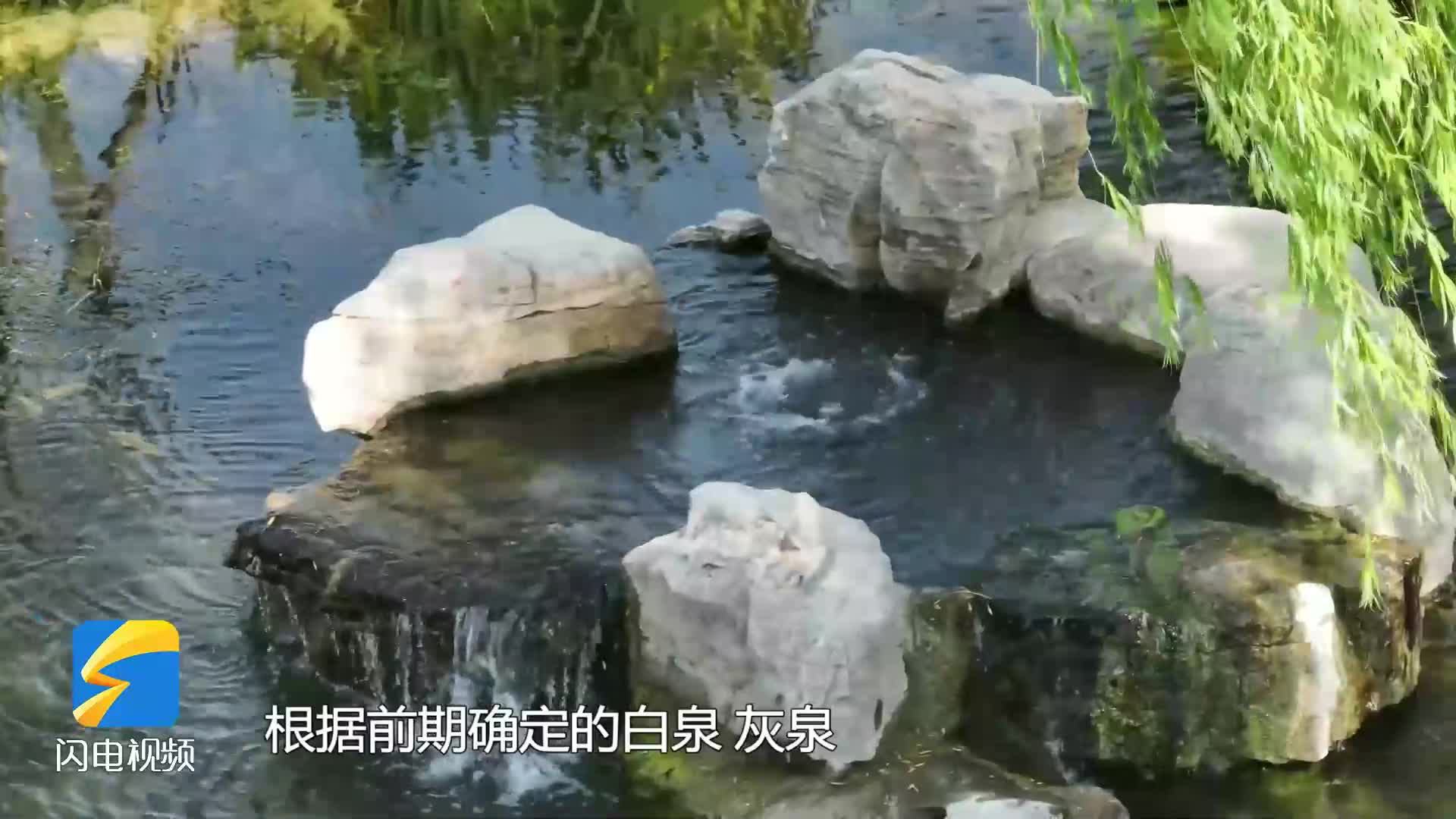重返故宮博物院成立“第一現(xiàn)場(chǎng)”
來源:光明日?qǐng)?bào)
2025-05-24 14:29:05
原標(biāo)題:重返故宮博物院成立“第一現(xiàn)場(chǎng)”
來源:光明日?qǐng)?bào)
原標(biāo)題:重返故宮博物院成立“第一現(xiàn)場(chǎng)”
來源:光明日?qǐng)?bào)
故宮博物院我們可能很熟悉,但其開啟我國(guó)現(xiàn)代博物館事業(yè)這段歷史,絕大部分人都知之甚少。我也是懷著同樣的探究之心,悉心拜讀《故宮掌門人1925-1949》之后,才有一種豁然開朗、撥云見日的感覺,深深體會(huì)到七位故宮早期掌門人的卓識(shí)見地、思想境界和無畏的奉獻(xiàn)精神。故宮博物院開創(chuàng)了由私而公的博物館歷史新紀(jì)元,故宮人把國(guó)寶文物與民族和國(guó)家的命運(yùn)關(guān)聯(lián)起來,他們這種“視國(guó)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深深打動(dòng)了我。
辛亥革命后,清宮是遜帝溥儀的住所,他在此居住生活了13年。1924年馮玉祥發(fā)動(dòng)“北京政變”驅(qū)逐溥儀出宮,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huì),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化私為公,成為全社會(huì)的共有財(cái)產(chǎn),由此開啟了中國(guó)現(xiàn)代博物館事業(yè)的新肇端,這也是本書的敘述起點(diǎn)。“化私為公”在當(dāng)時(shí)是一件大事,當(dāng)日北京市民紛紛涌入故宮,可謂“萬頭攢動(dòng),游客不由自主”。下午二時(shí),故宮博物院開幕典禮在乾清宮前隆重舉行,莊嚴(yán)宣告故宮博物院成立,數(shù)千人出席了典禮。本書指出,“紫禁城由皇宮轉(zhuǎn)向博物院,所代表的是一種由國(guó)家權(quán)力所認(rèn)可的主體記憶,既是去除帝制合法性的途徑,也能夠借此向民眾滲透破除帝王權(quán)威、掃除舊有勢(shì)力的觀念,從而嚴(yán)厲地摧毀皇家權(quán)威和尊嚴(yán)。”故宮博物院是時(shí)代的產(chǎn)物,也是中華文明視野更新的成果,是諸多有識(shí)之士奔走努力、呼吁抗?fàn)幍慕Y(jié)果,故宮形象的演變不僅與此一時(shí)期的政治、軍事、文化和社會(huì)各方面的歷史進(jìn)程息息相關(guān),還折射出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社會(huì)意識(shí)、思想觀念與國(guó)家追求,反映了封建與民主、帝制與共和、私有與公有、國(guó)家與團(tuán)體等種種歷史現(xiàn)象,這種糾纏與“褶皺”引人深思。
我們通常以為,驅(qū)逐遜帝溥儀出宮成立故宮博物院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可事實(shí)卻充滿曲折和艱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1925年9月29日,李煜瀛召集清室善后委員會(huì)會(huì)議,討論并通過了籌備會(huì)起草的《故宮博物院臨時(shí)組織大綱》及《故宮博物院臨時(shí)董事會(huì)章程》《故宮博物院臨時(shí)理事會(huì)章程》。決定以溥儀原居住的清宮內(nèi)廷為院址,以斷絕溥儀復(fù)宮的可能,保護(hù)國(guó)寶安全;考慮從清宮接受的公產(chǎn)多為古物和圖書,而世界各大博物館也大多藏有古物及圖書文獻(xiàn),因此規(guī)定博物院設(shè)“古物”“圖書”兩館,采取董事會(huì)監(jiān)督制和理事會(huì)管理制,并對(duì)董事會(huì)、理事會(huì)的職權(quán)與義務(wù)做出了詳細(xì)的規(guī)定。“活故宮”是李煜瀛建設(shè)故宮博物院的理念,這與其留法時(shí)期曾接受法國(guó)各類博物館等文化設(shè)施的熏陶有關(guān),這是一個(gè)非常超前且有長(zhǎng)遠(yuǎn)建設(shè)者意識(shí)的理念。就此,作者指出,“李煜瀛不僅是故宮博物院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而且為故宮博物院各項(xiàng)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xiàn)。”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故宮博物院的第一位掌門人李煜瀛以及董事易培基被段祺瑞政府通緝而被迫外逃,莊蘊(yùn)寬于危難中接手成為第二位掌門人,從4月初到7月底出面維持故宮博物院院務(wù),短短4個(gè)月,克服了諸多難以想象的困難。譬如,正是莊蘊(yùn)寬的斡旋,阻止了直魯聯(lián)軍進(jìn)駐故宮,這對(duì)于故宮文物的保管以及發(fā)展有著不可盡述的價(jià)值,可謂功莫大焉。本書作者指出:“從清室善后委員會(huì)成立開始,莊蘊(yùn)寬就與故宮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三一八’慘案后,故宮博物院理事長(zhǎng)李煜瀛遭通緝,新推委員長(zhǎng)盧永祥沒有到職,莊蘊(yùn)寬以副委員長(zhǎng)出面擔(dān)當(dāng)重任,兩拒故宮駐軍,堅(jiān)持點(diǎn)交文物,體現(xiàn)了一個(gè)故宮守護(hù)者始終不離不棄舍身庇護(hù)的擔(dān)當(dāng)精神,在故宮博物院最初的創(chuàng)建以及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的作用。”從中可見作者的拳拳之心,以及秉筆直書的歷史精神。作者對(duì)曾經(jīng)作為故宮掌門人的趙爾巽、江瀚、王士珍等人同樣基于歷史事實(shí)給予了相應(yīng)的篇幅,作出了實(shí)事求是的評(píng)價(jià)。
在故宮掌門人中,馬衡是本書作者大書特書之人。因院長(zhǎng)易培基被彈劾,馬衡在1933年7月15日召開的故宮博物院理事會(huì)上被委任代理院長(zhǎng)職務(wù),7月16日即赴滬,1934年10月任院長(zhǎng)。馬衡院長(zhǎng)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人事改革、建章立制、文物點(diǎn)驗(yàn)、修建故宮博物院南京文物保存庫(kù)、參展倫敦中國(guó)藝術(shù)國(guó)際展覽會(huì)、故宮文物西遷、存蜀古物返還南京、接受古物陳列所與故宮復(fù)原、拒不赴臺(tái)與保護(hù)故宮文物等諸多重要事件。其中,參展倫敦中國(guó)藝術(shù)國(guó)際展覽會(huì)、故宮文物西遷格外值得關(guān)注。倫敦中國(guó)藝術(shù)國(guó)際展覽會(huì)從1935年11月28日開幕,至1936年3月7日結(jié)束,歷時(shí)近4個(gè)月時(shí)間。其間舉辦過20多次有關(guān)中國(guó)藝術(shù)品的演講會(huì),觀眾十分踴躍,多達(dá)42萬人次,創(chuàng)下了皇家藝術(shù)學(xué)院的展覽記錄。英國(guó)國(guó)王喬治五世及王后也親自觀看展覽,還有從歐洲各地甚至美洲趕來的參觀者,都驚嘆于中國(guó)藝術(shù)品的古雅精美。
文物西遷萬里關(guān)山,困難重重,多次險(xiǎn)遭滅頂之災(zāi),卻都化險(xiǎn)為夷,造就諸多奇跡,可謂“天佑國(guó)寶”。故宮文物西遷有著延續(xù)民族文化命脈的意義,同時(shí)也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培育和形成了故宮人“視國(guó)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這是將故宮文物與中華民族的命運(yùn)關(guān)聯(lián)起來,與民族獨(dú)立和民族尊嚴(yán)關(guān)聯(lián)起來。尤為可貴的是,這期間還赴蘇聯(lián)參展一次,1939年9月24日抵達(dá)莫斯科,1940年1月2日,中國(guó)藝術(shù)展覽會(huì)在莫斯科開幕,1941年3月在列寧格勒展出,1942年9月8日展品回到重慶。此次展覽由中蘇文化協(xié)會(huì)和蘇聯(lián)文化協(xié)會(huì)共同促成,影響空前,起到了戰(zhàn)時(shí)促進(jìn)兩國(guó)團(tuán)結(jié)的作用。此外,為鼓舞抗戰(zhàn)士氣,在重慶和貴陽的展覽都非常成功,各界爭(zhēng)相參觀。這一系列展覽活動(dòng),如馬衡院長(zhǎng)所說:“結(jié)果不獨(dú)在闡揚(yáng)學(xué)術(shù)與國(guó)際聲譽(yù)方面,已有相當(dāng)收獲,即于啟發(fā)民智、增進(jìn)一般民族意識(shí),亦已有影響,成效頗彰。”書中種種記述,令人深刻感受到故宮博物院一路走來的艱辛不易,也升騰出一股發(fā)自內(nèi)心的敬佩之情,這正是一種道統(tǒng)賡續(xù)和文化托命!
隨這段歷史一路讀下來,感覺本書有兩個(gè)最鮮明的特點(diǎn):一是忠于史實(shí)的精神。該書為我們厘清了故宮博物院早期發(fā)展中的紛亂頭緒,為了解故宮歷史理出了一條清晰的線索,勾畫出一幅清晰的發(fā)展地形圖,使我們得以清晰地洞察故宮博物院發(fā)展的脈絡(luò)。在作者娓娓道來中澄清了諸多不實(shí)傳聞以及子虛烏有之事。其敘述有章法,講究邏輯性,有著對(duì)史學(xué)精神的傳承與追求。二是本書體現(xiàn)了作者深厚的文獻(xiàn)資料爬梳和考據(jù)功夫,史料豐富,考據(jù)扎實(shí),包括經(jīng)費(fèi)的來源和使用都一一道來,甚至附上不少原始文獻(xiàn),其對(duì)真實(shí)性的追求頗有現(xiàn)場(chǎng)感。書中所附精美插圖,舊報(bào)紙、老照片和手稿的影印件,為本書增色不少,也頗有趣味。究其意義和價(jià)值,正如作者所云:介紹這些掌門人的生平行事,既是對(duì)他們的一種紀(jì)念,也是對(duì)故宮博物院歷史的一種尊重。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要保護(hù)好這座承載中華文明的故宮,實(shí)有諸多不易,并對(duì)這些文明守護(hù)者生出由衷的敬意。
(作者:范玉剛,系山東大學(xué)特聘教授)
想爆料?請(qǐng)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chéng)邀合作伙伴。
山東商河實(shí)施“出彩媽媽?shí)彙背惨砉こ?/a>
- 中國(guó)婦女報(bào)全媒體記者姚建發(fā)自濟(jì)南近日,山東省濟(jì)南市商河縣召開“出彩媽媽?shí)彙本蜆I(yè)模式推進(jìn)會(huì)。中國(guó)婦女報(bào)全媒體記者從推進(jìn)會(huì)上了解到,商...[詳細(xì)]
- 中國(guó)婦女報(bào) 2025-05-24
祁連山國(guó)家公園青海片區(qū)冰川面積和冰儲(chǔ)量呈縮減態(tài)勢(shì)
- 本報(bào)訊近日,青海省林業(yè)和草原局、省氣象局、祁連山國(guó)家公園青海省管理局聯(lián)合發(fā)布《祁連山國(guó)家公園青海片區(qū)生態(tài)氣象公報(bào)》。數(shù)據(jù)顯示,2024...[詳細(xì)]
- 工人日?qǐng)?bào) 2025-05-24
對(duì)博物館的愛正在“升級(jí)”
- 近日,國(guó)家文物局發(fā)布2024年我國(guó)博物館事業(yè)發(fā)展最新數(shù)據(jù)。其中,三組數(shù)字既展現(xiàn)出博物館事業(yè)的蒸蒸日上,又顯示出國(guó)民文化消費(fèi)正在經(jīng)歷結(jié)構(gòu)...[詳細(xì)]
- 人民日?qǐng)?bào) 2025-05-24
讓國(guó)寶回家路更順暢
- 關(guān)于非法出境流失的過程,北京大學(xué)教授李零在他的《子彈庫(kù)帛書》一書中進(jìn)行了詳細(xì)梳理。根據(jù)他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該文物流失扎實(shí)完整的證據(jù)...[詳細(xì)]
- 人民日?qǐng)?bào) 2025-05-24
來,看看機(jī)器人的“類人生活”(瞰前沿)
- 人形機(jī)器人,正加速“跑”進(jìn)我們的生活。有人好奇,為什么要把機(jī)器人做成人的模樣。機(jī)器人也有“大小腦”嗎[詳細(xì)]
- 人民日?qǐng)?bào) 2025-05-24
助力玫瑰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
- 山東省棗莊市薛城區(qū)政協(xié)“有事‘棗’商量‘心’事咱有約·聚力玫瑰文化產(chǎn)業(yè)做大做強(qiáng)美麗經(jīng)濟(jì)”協(xié)商活動(dòng)在玫瑰園舉行[詳細(xì)]
- 人民政協(xié)報(bào) 2025-05-24
立足崗位促進(jìn)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 耕地是最寶貴的資源,是糧食生產(chǎn)的命根子。王娟惠作為浙江省桐鄉(xiāng)市崇福鎮(zhèn)東安村村委會(huì)主任、村級(jí)田長(zhǎng),保護(hù)好耕地是她的一項(xiàng)主要工作。她介...[詳細(xì)]
- 農(nóng)民日?qǐng)?bào) 2025-05-24
“你看這麥穗,顆粒飽滿”
- “小滿小滿,麥粒漸滿”。即墨區(qū)段泊嵐鎮(zhèn)后寨村種糧大戶李培珂在自家麥田俯身察看長(zhǎng)勢(shì),他告訴記者,今年又是個(gè)豐收年。在段泊嵐鎮(zhèn)劉家莊村...[詳細(xì)]
- 農(nóng)民日?qǐng)?bào) 2025-05-24
四季有鮮果 富民新路徑
- 眼下,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鹽池縣花馬池鎮(zhèn)特色溫棚水果產(chǎn)業(yè)迎來豐收旺季。如今村里的溫棚成了大家的“聚寶盆”,農(nóng)戶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花馬池...[詳細(xì)]
- 農(nóng)民日?qǐng)?bào) 2025-05-24
創(chuàng)新技術(shù)破解豇豆農(nóng)殘難題
- 豇豆是我國(guó)熱帶和亞熱帶地區(qū)的主要特色蔬菜,具有喜溫、耐熱的特性,因其風(fēng)味獨(dú)特、營(yíng)養(yǎng)豐富和耐儲(chǔ)藏等優(yōu)點(diǎn)備受大眾喜愛。熱區(qū)高溫高濕的氣...[詳細(xì)]
- 農(nóng)民日?qǐng)?bào) 2025-05-24
新中國(guó)成立初期農(nóng)村變遷研究的力作
- 《承載與重塑 新中國(guó)成立初期的農(nóng)村變遷》一書,以黨的農(nóng)業(yè)政策與鄉(xiāng)村社會(huì)變遷關(guān)系為主線,客觀梳理這一時(shí)期黨的一系列發(fā)展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路線...[詳細(xì)]
- 農(nóng)民日?qǐng)?bào) 2025-05-24
- 1央視《新聞聯(lián)播》點(diǎn)贊山東:以科技賦能推動(dòng)文旅產(chǎn)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
- 2濟(jì)南推出“好辦車管”服務(wù)套餐
- 3央視《新聞聯(lián)播》關(guān)注:第四屆全球媒體創(chuàng)新論壇在山東舉行
- 4公安系統(tǒng)榮獲2025年度 中國(guó)青年五四獎(jiǎng)?wù)隆⑿聲r(shí)代青年先鋒獎(jiǎng)名單
- 5深化依法治教保障學(xué)生合法休息權(quán)益
- 6《經(jīng)濟(jì)日?qǐng)?bào)》頭版聚焦山東港口青島港:全面提升開放能級(jí)
- 72025山東省文旅產(chǎn)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大會(huì)即將啟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