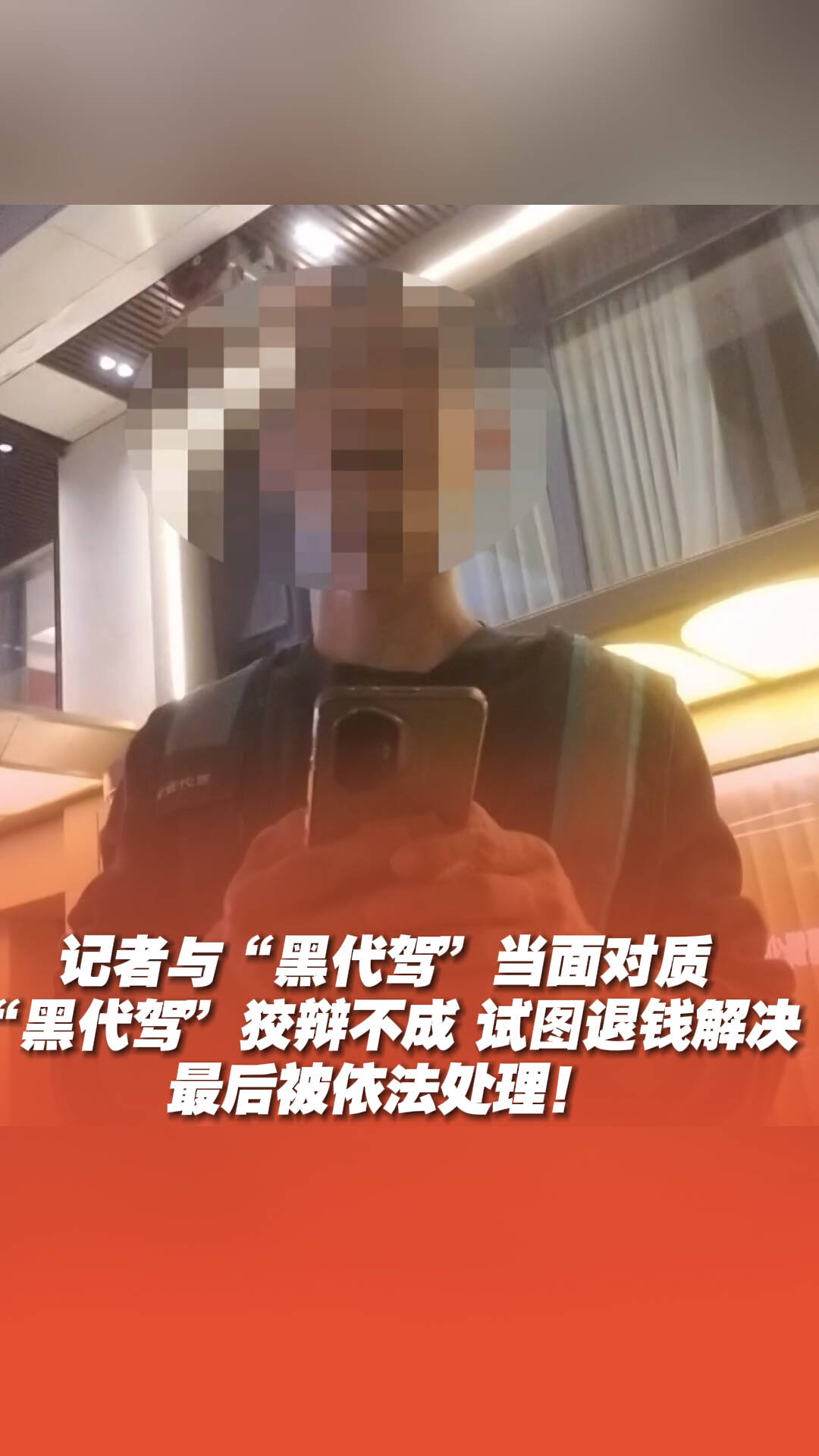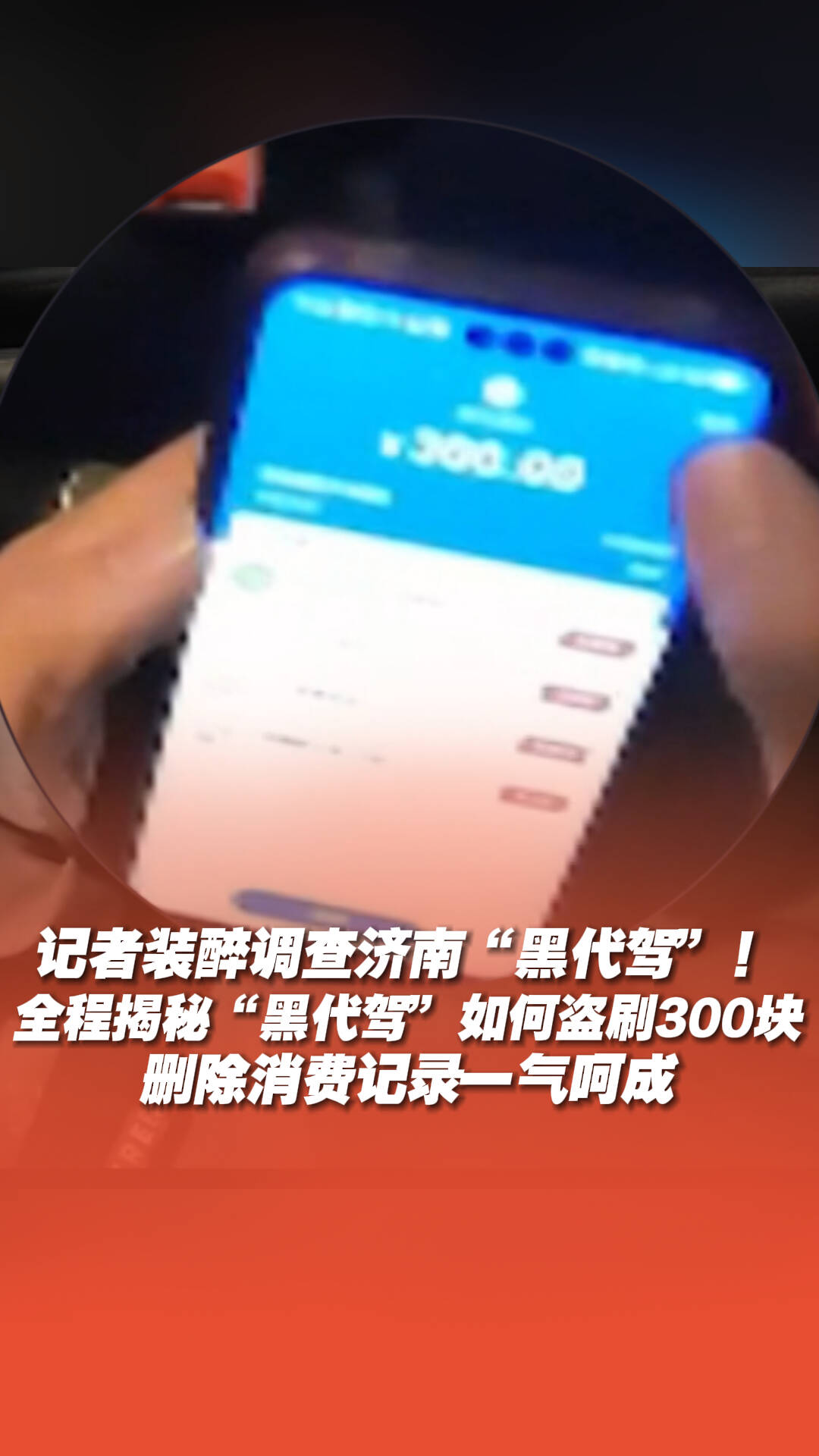【我是這樣做學問的】恩師帶我步入社科之路
來源:光明日報
2025-05-29 09:38:05
原標題:【我是這樣做學問的】恩師帶我步入社科之路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我是這樣做學問的】恩師帶我步入社科之路
來源:光明日報
【我是這樣做學問的】
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高考的恢復(fù),“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號召,激勵無數(shù)學子發(fā)奮苦讀。
在那個火熱的年代,我在甘肅省靜寧縣威戎中學念高中。學校距離縣城40多里,坐落在葫蘆河?xùn)|岸。群山環(huán)繞中,安裝了玻璃窗的教室,在晚自習日光燈的照耀下放出明亮的光,再加之好幾位老師的到來,吸引周邊十里八鄉(xiāng)山區(qū)的初中生,翻山越嶺跨鄉(xiāng)前來求學。
我有幸趕上時代的列車,也有幸進入重點班成為王子郭老師的學生。他是學生們公認的語文權(quán)威,一開講,就能將我們這些凍得縮成一團的學生帶入課文所描繪的社會場景,開啟大家的智慧之門。在那個偏遠的高中,他那一手剛勁的歐體板書,一腔播音員一樣的普通話,點燃了無數(shù)學生的求知欲。
我深受王老師的影響。他穿行過許多歷史的驛站,將人生的歷練融會貫通在課文的思想深處。講《陳涉世家》,他會問大家:為什么陳勝在耕田時會說“茍富貴勿相忘”,但在稱王后卻忘卻了初衷?講《阿Q正傳》,他會問大家:為什么阿Q被趙太爺打了會跑,但卻與王胡大打出手,與小D更會殊死纏斗,非要分出勝負?為什么身處同一階層的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會這樣激烈?在那個死記硬背標準答案以通過高考的年代,王老師提出的這些問題,讓學生們在入睡前熱烈討論。我那時就想,如果有朝一日能夠深造,一定要研究王老師提出的這些問題。
堅定我以學術(shù)為志業(yè)的那棵樹苗,則栽在王老師講《報任安書》的那堂課上。他極其推崇司馬遷,說他是古往今來的第一學問家。他引用司馬遷的話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王侯將相也任由雨打風吹去。但文王演《周易》,仲尼傳《春秋》,屈原賦《離騷》,丘明作《國語》,不韋留《呂覽》,韓非撰《說難》等,才真正留下歷史瑰寶。王老師多次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如果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而讀書,為人民的幸福安康而考大學、做研究、奉獻自己的青春,那么,就易于在目的論意義上使自己的人生接近“泰山”。
受王老師影響,我如愿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歷史檔案專業(yè)。學校的陳智為老師,平易近人、知識淵博、幽默詼諧,善于聯(lián)系具體實際講解深奧的理論。課間休息時,他總與同學們聊天,關(guān)心每位同學的成長。他說我能坐得住,有用心讀書的前途,將來有可能成為做學問的好苗子。實習時,陳老師專門為我們聯(lián)系到浙江嘉興市委辦公室讀檔案卷宗。我在那里用2個月時間整理了土地改革與劃分階級成分的文件材料,比較系統(tǒng)地梳理了農(nóng)民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的微觀和中觀歷史脈絡(luò),初步勾畫了當時農(nóng)村的社會結(jié)構(gòu)圖。
1995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社會學系,師從李培林老師學習應(yīng)用社會學。李老師畢業(yè)于巴黎第一大學,是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留洋歸國的博士。他一到社會學研究所,就隨陸學藝老師一起掛職于山東陵縣。他曾對我說,只有了解對象世界才能建構(gòu)對象世界。我一邊聽從他的指導(dǎo)讀經(jīng)典文獻、做讀書筆記,一邊通過調(diào)研彌合理論與現(xiàn)實的距離。
1996年,與我同在研究生院讀書的黨國英老師邀我參加民政部組織的“百名博士百村行”活動。我提交的以社會學調(diào)查方法為支撐的調(diào)研報告被評為優(yōu)秀調(diào)研報告。時任國務(wù)院副總理姜春云同志在紫光閣主持座談會,并舉行頒獎儀式。社會學家雷潔瓊先生為我頒獎時,親切勉勵我畢業(yè)后一定要做研究。雷先生一再說,鄧小平同志講社會學要補課,主要補的是人才的課。只有培養(yǎng)好接班人,才能形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創(chuàng)所所長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社會繼替”,建設(shè)好我們中國自己的社會學。
1997年,我被選派到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qū)掛職鍛煉。掛職期間,我受民政部閻明復(fù)同志委托,調(diào)研留守貧困兒童的學習狀況,意外發(fā)現(xiàn)各個小學里男生多、女生少,且呈現(xiàn)年齡越小年齡段性別比越高的趨勢。我結(jié)合微觀調(diào)研與宏觀數(shù)據(jù)寫了《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原因與對策》一文,發(fā)表在《社會學研究》。這是一篇較早反思計劃生育政策執(zhí)行中可能存在“負功能”的文章,也成為后來這一領(lǐng)域研究的高引用文本。意識到文章中的建議能夠轉(zhuǎn)化為國家的重大決策,我第一次對做學問充滿了使命感和自豪感。
1998年博士畢業(yè)后,我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研究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名家云集、人才輩出。我跟在各位前輩的后面,努力爬行,亦步亦趨。書山有路,學海無涯。我雖然資質(zhì)不高,但努力克服前行的懈怠感。聽前輩們的講座、讀碩學大儒的文章,使我產(chǎn)生新的動力,深化自己的研究。
小時候放羊,我經(jīng)常坐在一個小山包上做“白日夢”。但無論如何做夢,都沒有夢想到我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個大書山上做學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老實說,從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我的夢想。在不經(jīng)意間,我的人生融入改革開放之后的學術(shù)傳承中,這增加了我做學問的崇高感。
我感恩求學過程中遇見的每一個恩師。他們不僅是我為學的指路人,也是我為人的榜樣。在我人生的每一個關(guān)鍵時刻,他們都為我指點迷津。每當我完成一篇文章,或者修改完一本書稿,看著那一行又一行文字表達的邏輯,就覺得在時光深處,為中國學術(shù)殿堂的建構(gòu)又增加了一抔土、一塊磚。
(作者:張翼,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學會會長)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推動電影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
- “今年,以《哪吒之魔童鬧海》《唐探1900》等為代表的春節(jié)檔讓電影市場充滿希望,尤其是《哪吒之魔童鬧海》對中國電影今后在創(chuàng)作、市場、海...[詳細]
- 經(jīng)濟日報 2025-05-29
氫能重卡商業(yè)化應(yīng)用“掛擋加速”
- 從氫能重卡車的交付,到全球首款工程化落地的液氫重卡的亮相;從氫能重型卡車在高原地區(qū)試車,到“氫走廊”上氫能重卡擔負起綠色物流重責,...[詳細]
- 經(jīng)濟參考報 2025-05-29
“卡通戰(zhàn)友”成為施教好幫手
- 近段時間,武警東營支隊官兵經(jīng)常湊在一起,討論剛剛收到的一組以卡通形象“武小東”“武小瑩”為主題的新漫畫作品。該支隊領(lǐng)導(dǎo)告訴筆者,當...[詳細]
- 解放軍報 2025-05-29
【社評】讓工會服務(wù)陣地成為傳遞溫度彰顯作為的高地
- 只有確保工會服務(wù)陣地因需而建,以質(zhì)求效,才能為職工提供更精準、更有效、更契合的服務(wù)。期待更多地方能夠從撤銷不合格驛站中得到啟示,加...[詳細]
- 工人日報 2025-05-29
村民“小劇場”,講述身邊事
- 幾乎每個周末,山東濟寧市兗州區(qū)顏店鎮(zhèn)顏家村的小廣場都圍滿了人。村民自己編排的小劇目每周上演,講的都是大家身邊的故事。顏家村村民劉永...[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5-29
一曲“小調(diào)”何以傳唱世界(抗戰(zhàn)文藝作品巡禮)
- “人人那個都說哎沂蒙山好,沂蒙那個山上哎好風光……”近日,“中柬同心大道同行”中國柬埔寨人文交流活動的金邊現(xiàn)場,伴隨14歲的柬埔寨王...[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5-29
建強“四員”隊伍 為高標準農(nóng)田護航
- 近日,在山東省煙臺市萊陽市紀格莊村的高標準農(nóng)田里,連片的小麥正由綠轉(zhuǎn)黃,飽滿的谷穗,健碩的莖稈,長勢喜人。說著,李國華指了指胸前掛...[詳細]
- 農(nóng)民日報 2025-05-29
2025年第一批全國名特優(yōu)新農(nóng)產(chǎn)品公布青島“國字號”農(nóng)產(chǎn)品再添新成員
- 近日,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公布2025年第一批全國名特優(yōu)新農(nóng)產(chǎn)品名錄,青島“萊西大板栗”“萊西香菇”“龍泉雞蛋”“古峴蘑菇”4個產(chǎn)品榜上有名。至...[詳細]
- 農(nóng)民日報 2025-05-29
讓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金”
- 知識產(chǎn)權(quán)轉(zhuǎn)化運用是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的“關(guān)鍵一躍”,是打通科技強到產(chǎn)業(yè)強、經(jīng)濟強通道的“金鑰匙”。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專利轉(zhuǎn)化運用專項行動...[詳細]
- 中國市場監(jiān)管報 2025-05-29
破轉(zhuǎn)化壁壘 潤產(chǎn)業(yè)良田
- 水果可以先嘗后買,專利轉(zhuǎn)化也可以先用后付。荷凈凈化科技與齊魯工業(yè)大學合作,在一年免費試用期內(nèi)完成二維復(fù)合材料專利的工藝優(yōu)化,推動生...[詳細]
- 中國市場監(jiān)管報 2025-05-29
青州筑牢端午節(jié)食品安全防線
- 本報訊端午節(jié)臨近,為營造放心消費環(huán)境,山東省青州市市場監(jiān)管局提前部署,全面加強食品安全全鏈條監(jiān)管。結(jié)合消費熱點及往年抽檢情況,發(fā)布...[詳細]
- 中國市場監(jiān)管報 2025-05-29
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加強理論實務(wù)研究 深化國際法理論創(chuàng)新與實踐探索
-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決定》,站在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全局的戰(zhàn)略高度,系統(tǒng)部署了...[詳細]
- 檢察日報 2025-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