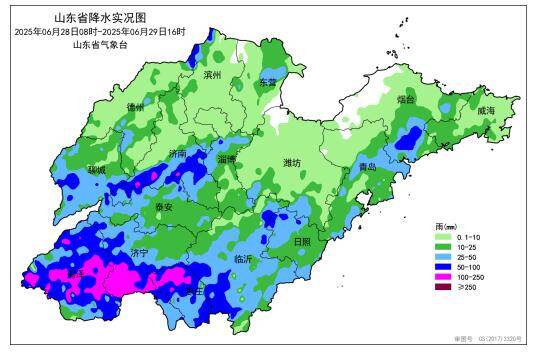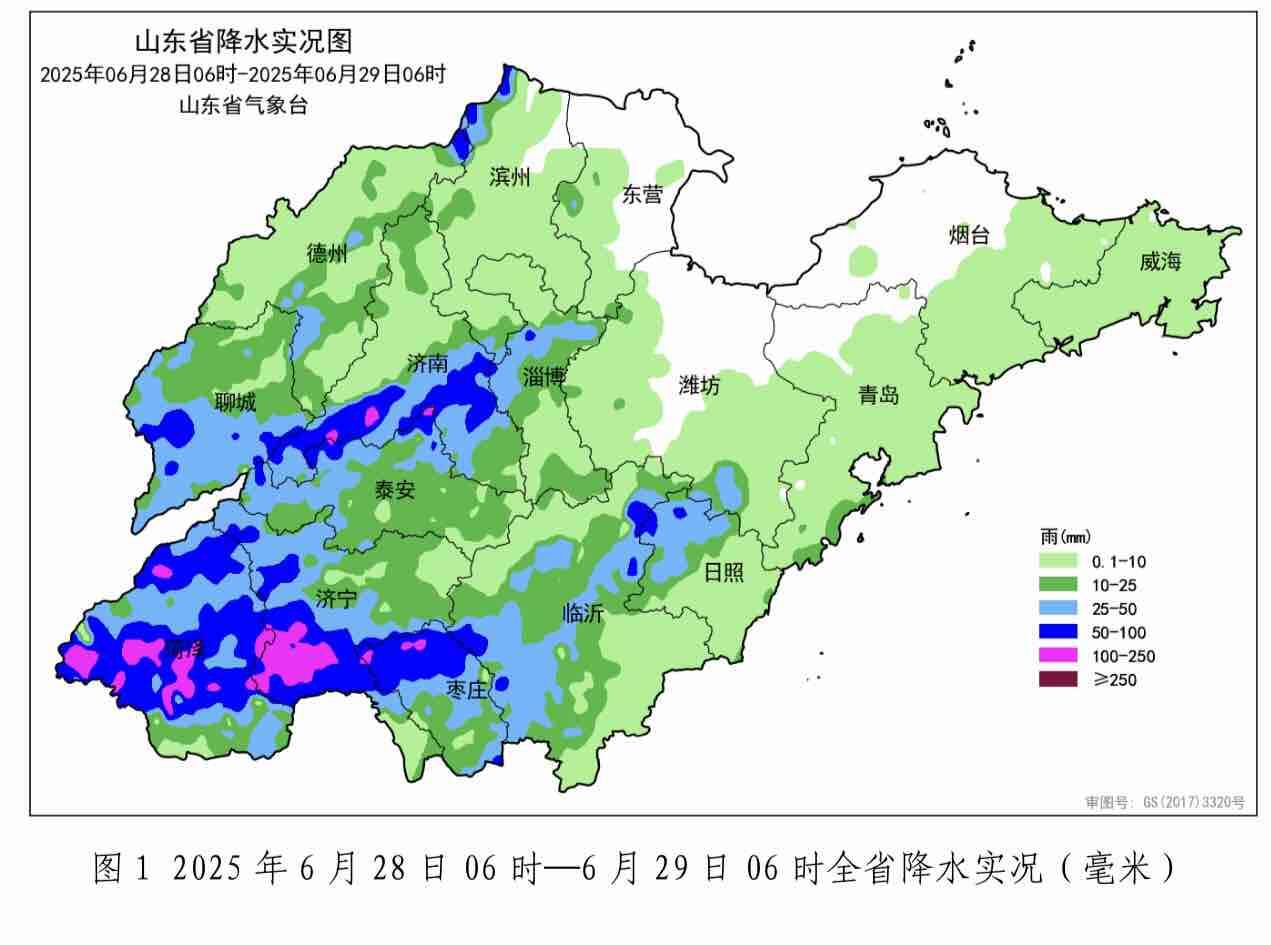在行刑反向銜接中把握好可處罰性原則的三條路徑
來源:檢察日報
2025-07-02 09:26:07
原標題:在行刑反向銜接中把握好可處罰性原則的三條路徑
來源:檢察日報
原標題:在行刑反向銜接中把握好可處罰性原則的三條路徑
來源:檢察日報
行刑反向銜接是檢察機關強化法律監督的一項創新機制。在開展行刑反向銜接工作中,檢察機關須嚴格把握可處罰性原則,通過對被不起訴人的行為進行行政違法性審查,進而決定是否發出予以行政處罰的檢察意見,實現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有機銜接。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實施《人民檢察院行刑反向銜接工作指引》(下稱《工作指引》)后,行刑反向銜接工作開展得更加順暢,但個案的差異性及案件審查重點的非標準化,為開展好這項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可處罰性原則的適用問題,成為當前行政檢察實務領域的關注焦點。本文從事實認定分層審查、和解案件區分處理、過罰相當具體裁量等三條路徑入手,探討可處罰性原則在行刑反向銜接工作中的具體適用,以期為檢察機關行政檢察部門高質效辦理行刑反向銜接案件提供借鑒。
事實認定分層審查
在事實認定方面,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往往各有側重。在行刑反向銜接工作開展過程中,有時存在刑事程序中認定的犯罪事實難以在行政處罰法律規范中找到相應處罰依據的問題。《工作指引》第八條明確要求“應當圍繞在案證據是否能夠證明被不起訴人實施了違法行為和是否具有行政處罰的法律依據進行審查”,這就要求在案件辦理中的事實認定層面,檢察機關行政檢察部門不應簡單地依附刑事程序的認定,而應在保持行政程序和刑事程序認定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以行政法律規范的構成要件為基準開展審查,堅持對行政違法行為的獨立判斷。
以羅某某非法捕撈案為例。羅某某為違法作業船舶供油并提供碼頭用于裝卸漁獲物,刑事程序基于共同犯罪理論,認定“羅某某提供碼頭”的行為構成非法捕撈罪的從犯,但行政違法行為審查則發現,該行為缺乏直接對應的行政罰則。若機械地依附刑事認定來替代行政違法行為審查,則可能導致“無法可依”;若進行其他定性(如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又可能引發“刑行認定沖突”的邏輯矛盾和使案件重新進入刑事程序的“死循環”。出現這種邏輯矛盾,本質上源于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在規范目的上的差異,即刑事司法以“法益保護”為核心,關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否達到犯罪標準,而行政執法以“秩序維護”為導向,更關注行為對行政秩序和規范的違反程度。
針對羅某某非法捕撈案,檢察機關行政檢察部門將羅某某的復合型違法行為拆解為“提供碼頭”和“非法供油”兩個獨立的行為,其中,“提供碼頭”行為雖然是在刑事程序中認定的犯罪事實,但該行為在行政處罰層面因缺乏相關依據無法予以處罰。而對于“非法供油”行為則有明確的處罰依據,即《山東省漁業資源保護辦法》第二十三條“向違法作業漁船供油、供冰的……給予警告,并處5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為此,檢察機關精準適用可處罰性原則,實現對行政違法行為的獨立性審查,針對“非法供油”行為提出予以行政處罰的檢察意見,使案件得到順利辦結。
和解案件區分處理
在刑事檢察部門向行政檢察部門移送的不起訴案件中,存在較多因賠償和解而作出的相對不起訴案件,對于該部分案件的審查,往往存在“或罰或不罰”兩種審查結果。《工作指引》第九條規定,“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后果的;當事人達成刑事和解或情節輕微并獲得被害人諒解的”,可以不提出檢察意見,此為“恢復性司法”理念在行刑反向銜接領域的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是通過加害人賠償、賠禮道歉等方式修復受損的社會關系,而行政處罰的目的包含警示和預防。如果當事人系偶犯、初犯,實施違法行為的目的和動機的社會危害性較小,且通過刑事和解的方式已經化解了矛盾,若再提出檢察意見給予行政處罰,則不符合可處罰性原則的適用要求。
以王某某故意毀壞財物案件為例。王某某醉酒后對被害人的指責心懷怨恨,于是實施了砸壞被害人家中財物的行為。因其積極賠償了被害人損失并取得了被害人諒解,亦未造成嚴重后果,檢察機關刑事檢察部門在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后,行政檢察部門經審查亦認為無需進行行政處罰,故檢察機關未發出對王某某進行行政處罰的檢察意見,避免了“過罰不當”現象的出現。而在某企業超標排放污水不起訴案中,某企業雖與周邊居民達成補償協議,但檢察機關仍建議行政主管部門給予行政處罰,理由是某企業的行為破壞了生態環境,需要通過行政處罰實現一定的警示效應,體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需要強調的是,賠償和解不罰的情況應限于侵害個人法益的案件,若違法行為損害了公共利益(如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等),或系累犯,或存在較大社會危害性,即使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仍需對該違法行為予以行政處罰,以維護公共秩序并達到震懾違法的效果。
總之,對于刑事和解不起訴案件,行政檢察部門在開展行刑反向銜接工作中應依據可處罰性原則進行區分處理,既確保過罰相當,又避免不刑不罰,真正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過罰相當具體裁量
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小過重罰”現象極易引發輿論關注。這一現象背后的本質,實際上是執法主體對“形式違法性”與“實質可罰性”的割裂,以及對“過罰相當”原則的片面理解。如何避免“小過重罰”現象的再次發生?這也是檢察機關在行刑反向銜接工作中務必重視的問題。對此,筆者的建議是把握可處罰性原則,對具體案件進行差異化區分。
行政處罰法第五條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因此,行刑反向銜接案件是否應當發出檢察意見,須結合違法行為的主觀過錯、行為類型、社會影響以及整改效果等進行綜合判斷。對于主觀過錯,應審查是故意違法還是過失違法,是否存在惡意規避監管等行為;對于行為類型,應審查是否屬于危害公共安全、生態環境等特殊領域的違法行為;對于社會影響,應審查是否可能引發效仿效應,破壞社會行政管理秩序;對于整改效果,應審查是否及時糾正違法行為,主動消除違法后果。對首次違法、后果相對輕微且主動改正的,可以適用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的“首次違法不罰”原則。對于違法的經濟價值較小,但具有潛在社會危害性的違法行為,則應堅持“該罰則罰”。如禁漁期捕撈100元海產品的行為,單獨從經濟價值上看屬于“小過”,但該行為明顯違反漁業法中關于禁漁期的規定,影響了海洋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如果不進行處罰,勢必引發效仿,具有潛在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對于這類違法行為,檢察機關應及時發出予以行政處罰的檢察意見。
綜上,檢察機關行政檢察部門在開展行刑反向銜接工作中,應當嚴格依據《工作指引》的規定,把握好可處罰性原則在具體案件中的適用,厘清刑事違法與行政違法的差異,重點做好和解案件區分處理,避免“小過重罰”和“過罰不當”現象出現,準確適用相關法律法規,讓可處罰性原則成為破解行刑反向銜接難題、提升行刑反向銜接工作質效的“金鑰匙”。
(作者單位:山東省膠州市人民檢察院)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山東巨野:構建綜合防治體系 精準打擊拒執行為
- 本報訊山東省巨野縣人民法院緊扣“公正與效率”主題,以“麟法善執”品牌為引領,從機制、聯動、質量、宣傳四個維度精準施策,全力打擊拒執...[詳細]
- 人民法院報 2025-07-02
2024年度全國稅務系統“四好”黨員
- 北京市稅務系統馬靜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西城區稅務局社會保險費和非稅收入科副科長喻欣欣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第一稅務分局大企業服務四...[詳細]
- 中國稅務報 2025-07-02
構建一流工科基礎課程教學育人體系
- 面對新工科建設對復合型人才培養的新要求,青島理工大學自2014年啟動工科基礎課程教學體系的系統性改革,教學團隊秉承“百折不撓、剛毅厚重...[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7-02
“荷”香四溢 育夢遠航
- 山東省曹縣附近有一座大型平原水庫——太行堤水庫,蓮藕種植面積8500畝,盛夏荷花盛開,被譽為“萬畝荷塘”,形成“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7-02
深化教學改革 點燃思維之光
- 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新建路小學是一所創辦于1926年、承載近百年教育文脈的老校,在新時代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浪潮中勇立潮頭,持續深化教育教學...[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7-02
“一千零一夜”的另一種寫法
- “童年的消逝”的嚴峻現實也給兒童文學創作提出了挑戰 兒童文學僅有童真、歡快、純凈、明確還不夠,也應體現思想的含混與深厚、生活的復雜...[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7-02

《人民日報》頭版關注:青島造西江24-7平臺上部組塊陸地完工起運
- [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7-02

《人民日報》關注山東日照:耕海牧漁,建設“藍色糧倉”
- [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7-02

《求是》刊發林武署名文章:打造現代海洋經濟發展高地
- 我們要深刻領會、堅定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海洋強國建設的重要論述和對山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堅持把海洋作為高質量發展戰略要地,奮力經...[詳細]
- 閃電新聞 2025-07-01
讓農業“壓艙石”分量越來越足(人民時評)
- 促進農業新質生產力進一步釋放,有待更多新農人主動適應現代農業規模化、智能化和專業化趨勢,在廣袤沃野發揮才干、展現作為今年的夏收迎來...[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7-01
二〇二五年全國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費季啟動
- 本報青島6月30日電2025年全國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費季主場活動30日在山東省青島市舉辦,正式拉開全國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費季的序幕。為貫徹落實...[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7-01
查找身邊隱患 共筑安全防線
- 玩“穿越”,四川編排情景劇《我在古蜀當焊工》,演示動火作業規范操作;解謎題,廣東設計互動游戲吸引市民參與隱患識別;上云端,南方航空...[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7-01
政策賦能+場景創新文旅市場活力迸發
- 本報記者趙熠如今年以來,我國持續提振文旅消費,從政策出臺到地方特色活動落地,多維度激發了市場活力,推動國內出游人次與消費金額雙增長...[詳細]
- 中國商報 2025-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