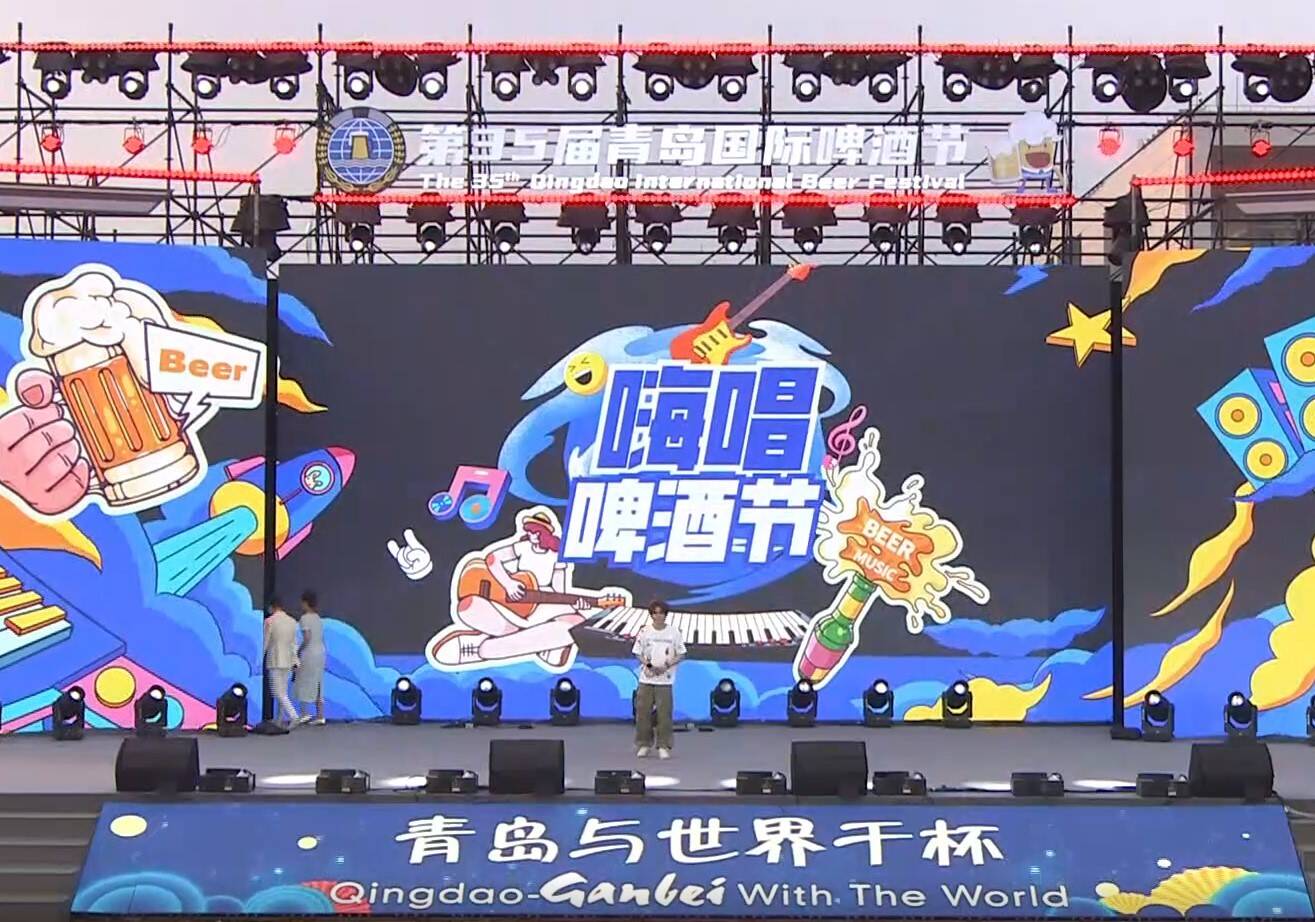如是造,如是作
來源:光明日報
2025-07-23 09:53:07
原標題:如是造,如是作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如是造,如是作
來源:光明日報
【學術爭鳴】
6月8日《光明日報》刊發的仝濤文章引發持續討論,學界出現百家爭鳴現象,有幸躬逢其盛,茲與各位分享我的思考過程,歡迎證偽。
一
先識字。仝濤將其中幾個字符識讀作“廿六年三月己卯”,之后,他在后續訪談中仍傾向于這個觀點。可是,這個時間點與“皇帝”一詞在時間上不匹配,引來若干質疑。細看其中被楷定成“六”的那個字,疑似“六”字的一撇更像是巖石的自然凹痕,如果把這個凹痕擋住,該符號是否更像“七”字?只要滿足以下條件:五大夫翳一干人行程安排得緊湊一些,“廿七年三月己卯”與“皇帝”不是沒有并存可能。之后,網上發布的高清照片,從中可見“廿”字中間尚有一豎,這與《里耶秦簡》中出現過的“卅”字相似,于是多位學者先后將該字識讀為“卅”。許多論者關注“三月己卯”,謂某年三月并無己卯,多據今人推定的歷表,如饒尚寬《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等推得始皇帝卅七年夏歷三月己卯在三月初二。如果推測無誤,當時表達常例應是“三月初吉”或“三月己卯初吉”,圖個吉利。秦歷三月己酉朔,當月無己卯,但四月己卯朔。這種大事張揚的官方行為理論上應使用秦歷,日歷表中未見三月己卯,或可作如下解釋:一是即使后來學者推定的日歷無誤,當時人使用時也未必能完全準確;二是萬一五大夫翳一行計算有誤呢?恰如魯濱遜漂流期間,自以為在逐日記錄,最后還是有誤差。所以,不能據此給石刻證偽。
“方”下一字,準確地說是半個,仝濤楷定作“士”,可是秦文字的“士”有這種寫法嗎?未見。也有論者釋讀作“支”,通“技”;劉紹剛《“昆侖石刻”獻疑》釋作“伎”,劉釗《我對昆侖刻石的看法》釋作“策”,這些于字形、字例俱無問題,唯刻石作者想表達的似以作“士”者為密,這一點頗堪玩味。信息不全,故不置疑。
還有“車”字,我初讀頗覺疑惑,畢竟此地不是天下之中洛陽,也不是軍事重地榆林、北地,非馳道所經之地。但我提醒自己,越是原始的工具,適配性越強,維修也越簡單,更不能低估權力的意志,“道九原,抵云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于是我自證其偽了,盡管仍然存疑:在秦制二十等爵中,五大夫位列第九,其排場與號召力是不能與秦始皇相提并論的。姜生《秦昆侖刻石考》謂“第七級的公大夫、第八級的公乘尚屬‘高爵’,第九級的五大夫更是如此”,則似理解有誤。
二
次消文。石刻見“一百五十里”,早期文獻有百里、百金、百谷、二/三百五十,卻未見“一百五十”,個別不能明確認定為早期文獻者如今本《尉繚子》中的詞例作不得數。有論者認為,該字上方巖石不規整,可能有破損,在理,所以不能排除“百”前為二、三的可能性。于是我這個證偽也隨即被證偽。姜生上文謂“原石所見,‘二’字上面一橫,雖僅存右端一小部分,但仍清晰可睹”,仔細辨認,不可必。仝濤倒是釋讀成“一”的,云:“從石刻地點向西行60公里,正是當今之‘星宿海’的位置……歷史上,星宿海一直被認為是黃河源頭所在。”直指黃河源,且言之鑿鑿。不知這里的“一直”起自何時?當年星宿湖的范圍是否與現在一致?進一步說,如果該字非“一”,是否會動搖相關結論?王子今《昆侖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反復引述清人文獻中的“昔人所刻篆文”為之證實,唯此“昔人”篆文的價值當隨具體的時間點認定。需要思考的是,石刻撰文者想表達什么。以上質疑都無關于石刻的真偽。
前云“五大夫臣翳(末字僅見上端,此據下一“翳”字推斷)”,后云“翳”,則此“臣”系翳自稱。如果系他人轉述,不會出現“臣”字。故可以推斷:該石刻為五大夫翳自述,同時排除事中事后他人記錄、描述的可能性,這是討論該石刻寫作背景的一個前提。
至此,從文字、詞法、句法、語篇等方面,本人未發現該石刻有明顯作偽之跡,非“一眼假”。循無罪推定原則,假定該石刻為真。
三
假定該石刻為真,同時該石刻敘述者就是文中那個五大夫翳。以此為前提,是否可以推定以翳為首的團隊受始皇帝之命赴昆侖山采藥為一種有組織的國家行為?這種重大行動,行前是否應該有充分的攻略,且不限于預備刻工小組?《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帝國之勢力“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瑪多在臨洮之西,選擇今天的高速公路,少說也在700公里之上。那么,團隊到一個化外之地,是否同時負有宣威和宣慰之責?因此,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的皇權意志是否應該在這一通石刻中得到體現?包括但不限于石刻的體積、從整體到細部的視覺效果、文字的選擇、字的大小、比例、字距、行距、版式、誰撰文、誰書丹、是否以及何人署名……最重要的,則是其中的內容:譬如同期泰山刻石、瑯琊刻石、之罘刻石等幾通秦刻石普遍具有的頌秦德、表功績、明法規的內容,其中作者的精神面貌無不是被嚴格規訓過的,同時也無不出之以規訓的面目與聲氣。五大夫翳卻是個例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為五大夫,又想例外?難。所以,我傾向于相信這個獨當一面的五大夫翳,這個西行的皇帝使臣是有最起碼的政治覺悟的,連刻工這種后勤保障都已預為籌謀,追求揚名立萬的同時,不至于把平時熟知的高頭講章拋諸腦后。在皇權的加持下,在4300米的高海拔地區,在極寒天氣的野外,在堅硬的層狀粉砂巖上,興師動眾,到頭來,兩度署名之后,只留下一個“□前□可一百五十里”的交通標識牌?如果此文系翳自撰,此石刻系翳親自監制,該當何罪?如果是他人代筆,則此人又是何居心?此不能自洽者一。
四
再討論五大夫翳團隊的使命—采藥,前面也已假定為真。胡文輝《從文本看“采藥昆侖”石刻的疑點》從“采藥”一詞在文獻中出現的時間點偏晚提出疑問,該文所引包伯航文,則指秦漢時的“藥”字偏向指藥品,基本不指藥材,兩文都認為其時藥不能采。我跟進舉證。
先說“采”,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寫作“求”:始皇三十二年,“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三十五年,“求芝奇藥”“求仙藥”“求奇藥”;始皇三十七年,“求神藥”;皆未見“采”。后來的漢武帝與秦始皇有著同樣的志趣,《漢書·郊祀志上》載其“遣方士求神人采藥”,《漢書·郊祀志下》亦言“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此處始出現“采藥”,但依然不離“求神”“求仙”,態度虔誠恭敬,則在秦人的觀念中,此藥是否可“采”?閻焰據《里耶秦簡》認為該石刻出現以“采藥”為目的涉及最高統治階層的行為,并沒有那么突兀。其說貌似有理,但民間獻藥與皇帝欽命某官員采藥大有不同,官員銜皇命采藥,容易聯想到皇帝本人的健康需求,區別在于是否觸犯忌諱。
次說“藥”,求仙、尋仙在那個年代是高大上的活動。而采藥,與求仙、尋仙大別,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聯想。《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關于藥,每一次敘述都無關乎健康,只指向長生不老:“不死之藥”(始皇三十二年、三十五年)、“奇藥”(始皇三十五年)、“仙藥”(始皇三十五年)、“神藥”(始皇三十七年)。多少年以后,唐憲宗命一個叫柳泌的道士遠赴天臺山,后者“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雖然這是其真實使命,可柳道長明面上的身份是臺州刺史。《資治通鑒》也提到了“藥”,可那是“長生藥”,是“靈草”(見《通鑒》卷二四〇、二四一),絕無歧義。“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支(技、伎)采樂(藥)昆侖”,這種泛泛的且輕飄飄的表達,對神靈語帶輕慢,于讀者易啟疑竇。皇帝的健康狀況是國家頂級機密,《史記》載始皇帝“豺聲”,竊疑非生理性的,而是病理性的,蓋因其長期列鼎而食,青銅器中的鉛、砷等重金屬沉積在體內,出現各種慢性中毒癥狀,其中包括損傷喉返神經,致聲音嘶啞、顫抖,這是他從即位二十八年起一直滿世界求藥的原因。寡人有疾,一個五大夫,敢刻石以昭告天下?覷得我大秦律法如無物!此不能自洽者二。
五
最后說書寫與材料。因為上述兩個不自洽,前文提到的若干文字及書寫問題又被激活了。劉紹剛前文指出:“昆侖石刻橫畫的筆勢則或直或彎,在一個字中間也混雜了不同的筆勢,這就十分不協調、不自然。”這值得重視。
仔細辨認高清照片,發現“皇”“帝”“五”“三”“己”“車”“可”“百”“里”和“到”中,橫畫的各種筆勢奔涌而來,好一個大雜燴。同一個書手,在這么一小幅作品中,何以有這么多變化?兩個“羽”部,兩種起筆:前者先向下頓挫再向右平行走筆;后者輕細起筆,再向右上方略帶弧形行筆。兩個“五”字,前仰后平,第二畫,前者從上部橫畫的中間起筆,后者從末端起筆。各位論者不妨試試,是否有頻繁變換筆法的習慣與能力。“皇”字筆畫疏朗,緊接著的“帝”字卻拘謹局促,大小不成比例。“帝”字的首筆,只是一個飾筆,戰國古文字中,除楚系文字外,都寫成平直的短橫,這里卻出現了一個弧形,不免隨意。同一件作品中,“使”“翳”“己”“此”“可”筆力遒勁,筆法蒼老;“采”“月”則纖細羸弱。“帝”“樂”“百”結構致密,“采”“侖”卻疏松。惡劣條件下,確實不能跟瑯琊刻石、泰山刻石等相比,后者精選石材、深度預處理以及經由國家層面的書手、刻工最后完成,但是,官方的靜態書體,整飭法度的追求總是先于多變個性的表達,該石刻卻反之。凡此,皆指向一種可能性:該石刻書丹者非一人,甚至刻工的發揮和對墨跡的理解與把握也有高下。這或許就是劉紹剛揭出的缺少行氣的原因。那么,為什么要假眾手為之?
材料上,刻字所產生的微裂隙極易成為巖石風化擴展的起點,面對高寒地區的強烈日照、頻繁凍融、晝夜溫差,經過兩千多年,這些擾動結構未見顯著劣化,依然保持表面平整,字跡清晰,何以能夠?反而是四圍風化更嚴重,你道怪也不怪?假定兩千多年前該巖石尚未風化,則“皇帝”所在首列當右移二列,以取相對完整的石面。徐金超也提醒我,假定當時“皇帝”以下位置石塊尚未脫落,則“使”“五”二字當接續在“帝”字下方,而非另起,甚至“大夫”亦當在“五”下;假定當時已經脫落,則整個刻石區域當左移兩列,以取相對完整的石面。目前的版式安排疑系基于風化后石面的量身定制,讀者諸君以為如何?
(作者:俞志慧,系紹興文理學院教授)
(稿件統籌:本報記者 王笑妃、陳雪)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旅游休閑街區:近者悅,遠者來
- 近年來,不少旅游休閑街區變為熱門景點,逐漸成為城市文旅的新名片。我國街區數量龐大,具備一定規模的步行街或商業街超過2100條,歷史文化...[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7-23
鐵路公安積極排查隱患應對臺風等惡劣天氣
- 各地鐵路公安機關組織開展安全隱患排查,加強站車線巡邏檢查,積極宣傳疏導,全力搶險救災,維護良好秩序。各地鐵路公安機關密切與鐵路企業...[詳細]
- 法治日報 2025-07-23
孝子與仙女的傳奇背后
- 董永故事原來是說董永為奉養父親欠下巨額債務。“賣身為奴”的法律問題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文明古國的法律,都曾規定如果債務人不能及時清償債...[詳細]
- 法治日報 2025-07-23
警務協作讓隱匿26年嫌疑人顯形
- 本報訊記者顏愛勇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鄂溫克旗公安局以本地偵查起底為抓手,以外地多方協作機制為依托,開展命案積案攻堅工作,取得積極成...[詳細]
- 法治日報 2025-07-23
電動車盜竊案牽出28年前殺人案
- 本報訊記者李娜通訊員陳語彤于明辰近日,山東省濰坊市公安局高新區分局成功破獲一起電動車盜竊案,民警在審訊嫌疑人時敏銳察覺其虛構了身份...[詳細]
- 法治日報 2025-07-23
“君子食堂”:中式快餐在美成新寵(僑界關注)
- 西紅柿打鹵面、拌面、湯面……這些大多數中國家庭都會做的普通菜肴,近年來在美國吸引當地人紛紛排隊品嘗,很多粉絲成為常客。一個名叫“君...[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7-23
一場對話,圍繞城市展開
- 青島的紅瓦綠樹、明斯克的壯麗軸線、雷根斯堡的古城新韻、煙臺的仙境風光、拉各斯州的老城新生、達尼丁的多元文化……在山東青島市的海邊,...[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7-23
世界各地市長點贊青島
- 7月19日,2025“世界市長對話·青島”活動在山東省青島市舉行。作為活動的主辦方,青島以其獨特的魅力和開放的胸懷贏得了世界市長們的一致...[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7-23
避暑游上新 催熱“夏日經濟”
- 正值暑期,為推進全國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費季、豐富避暑旅游應季產品和特色活動、滿足廣大游客多樣化消費需求,傳統和新興避暑旅游目的地不斷...[詳細]
- 中國文化報 2025-07-23
濟南連續四年開展巾幗家政培訓
-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姚建發自濟南近年來,山東省濟南市婦聯深入實施“就業創業巾幗行動”,多渠道幫助婦女就業,取得明顯成效。近日,中國...[詳細]
- 中國婦女報 2025-07-23
將“全周期管理”理念融入案件查辦全過程
- 紀檢監察機關要聚焦提升依規依紀依法辦案質效,著力增強監督檢查、審查調查本領,嚴格按照權限、規則、程序開展工作,確保辦理的每個案件都...[詳細]
- 中國紀檢監察報 2025-07-23
山東德州陵城區加強農村集體“三資”監管
- 本報濟南7月22日電山東德州市陵城區紀委監委聚焦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將大數據手段運用到基層監督中,構建“侵占農村集體光伏發電項目資...[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