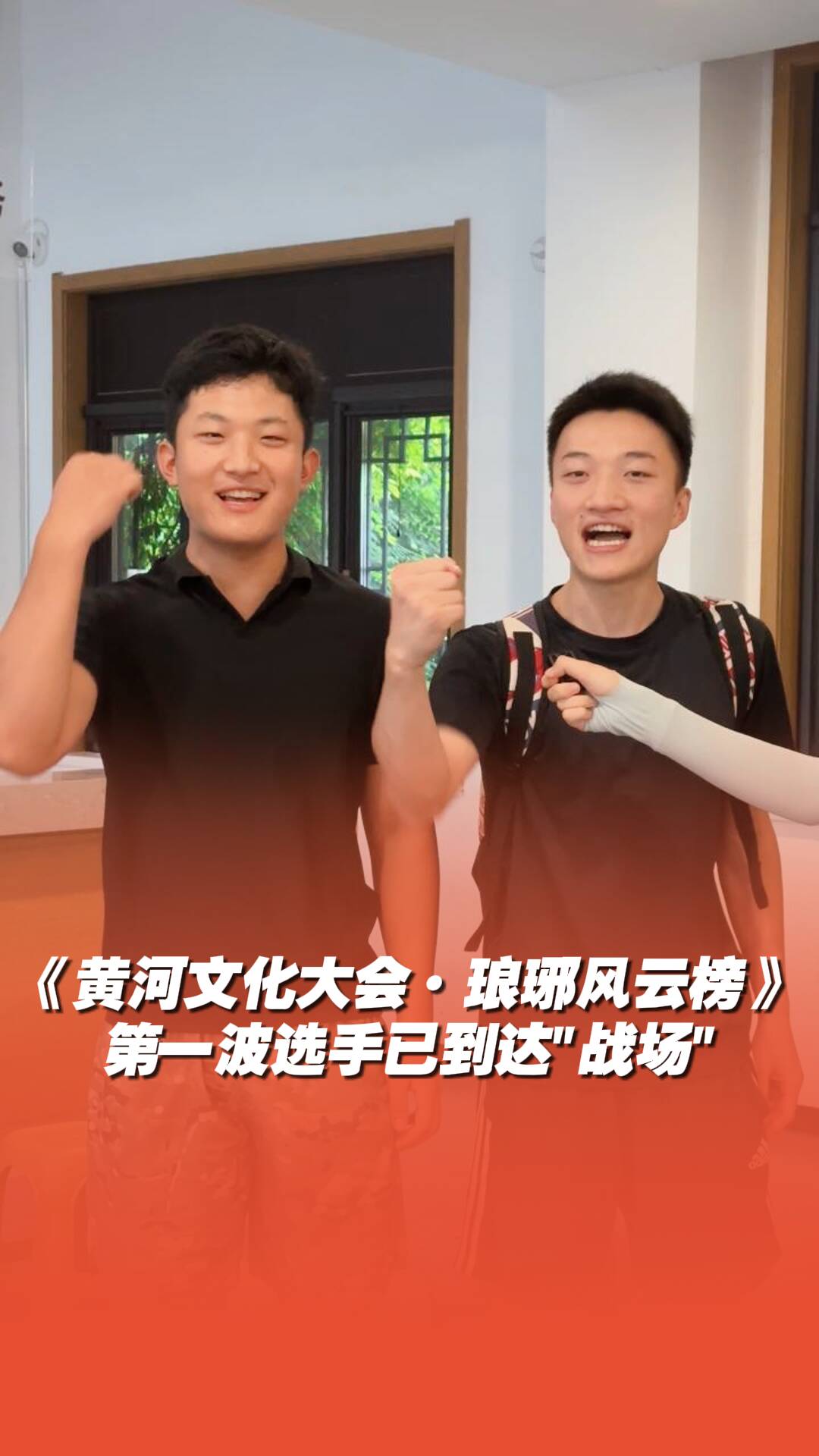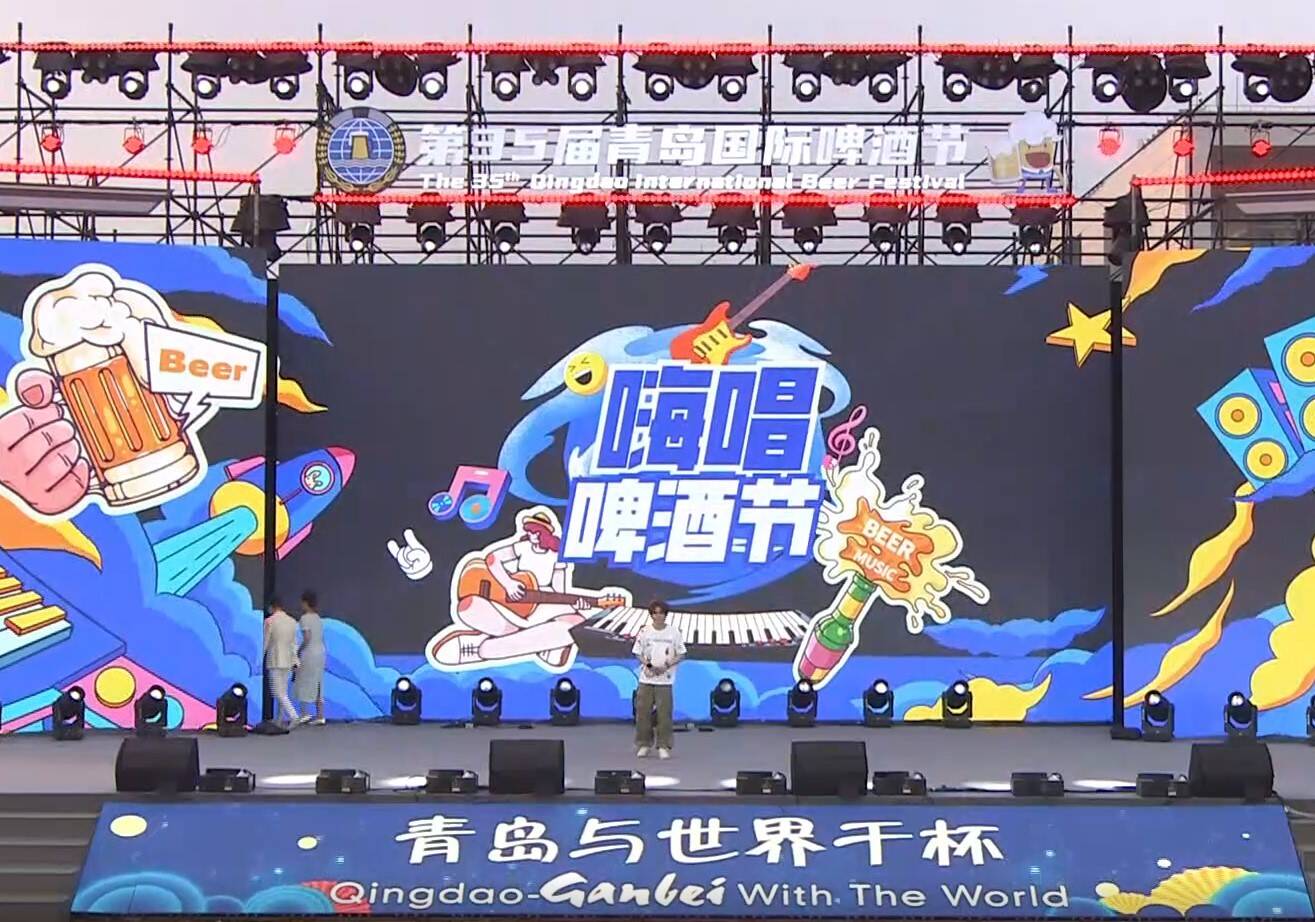東北淪陷區的抗日文藝宣傳橋頭堡
來源:光明日報
2025-07-25 09:03:07
原標題:東北淪陷區的抗日文藝宣傳橋頭堡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東北淪陷區的抗日文藝宣傳橋頭堡
來源:光明日報
為地下黨和淪陷區廣大左翼作家持續提供反滿抗日宣傳陣地的《國際協報》,在東北抗戰史上應占一席之地。《國際協報》是哈爾濱開埠以來影響力最大,輻射平(北京)、津、滬等大城市的報紙。該報文藝副刊前后三任主編裴馨園、方未艾、白朗,開辟了以筆作刀槍的反滿抗日文學園地,并通過副刊幫助東北作家群中蕭紅、蕭軍、舒群、羅烽等左翼作家在文壇崛起。蕭紅反映黑土地農民由起初渾渾噩噩、麻木不仁,進而覺醒奮起投向抗日陣營的《生死場》,其前兩節就是在《國際協報》上連載的。而蕭軍文學事業的起步,也始于《國際協報》,他在這一時期創作了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特刊發此文,紀念我國最早描寫淪陷區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小說《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誕生90周年。
一
在東北作家群中,蕭軍是最早同《國際協報》結緣的。
蕭軍在哈爾濱立足,文學事業起步,參與營救蕭紅及與蕭紅結合,助推蕭紅邁上文壇,都同《國際協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1932年2月,參加哈爾濱保衛戰失敗后無處可去、生活陷于困頓的蕭軍,給《國際協報》投寄了一篇題為《飄落的櫻花》的稿子。同時,他還給編輯部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的困境。稿件發表后,報社派人送來一封信,還有5元錢,并約蕭軍去報社見面。信中特別說明,錢是編輯個人對作者的敬意,談不上什么稿費。由此,蕭軍認識了江浙口音的小個子副刊編輯裴馨園。裴馨園很賞識蕭軍的文采,請蕭軍幫他編“兒童特刊”,并擔任該報的專訪記者。
不日,應裴馨園之邀,蕭軍從“明月小飯館”搬到了裴馨園家中,從此正式開始文學生涯。蕭軍啟用“三郎”作為筆名,開始為副刊撰寫各類稿件。裴馨園不僅滿腔熱忱地接待了蕭軍與因在吉林舒蘭發動兵變抗日而流落到哈爾濱的方未艾(方靖遠)這兩位落魄亡命人,還幫助蕭軍救助落難中的蕭紅。
1932年7月9日,正在《國際協報》社內編稿的裴馨園,收到了一位名叫張廼瑩(即蕭紅)的女性讀者的來信,信中述說她被軟禁在道外東興順旅館里,欠了幾百元的債還不了,旅館老板想把她賣到“圈兒樓”(妓院)去。她來信的目的是希望報社出面主持公道,從而救她脫險。
“我們都是中國人!”信中這一聲從社會底層饑寒交迫中的女性口中發出的呼喊,在日本侵略者鐵蹄粗暴踐踏我東三省大地的當口,讓人聽了,是如此振聾發聵!
裴馨園看完信后,當即放下手頭正在編的稿子,會同舒群等人前往位于哈爾濱道外正陽十六道街的東興順旅館探訪了蕭紅。3天后,也就是1932年7月12日的下午,裴馨園又接到了蕭紅打來的電話,說她在旅館里很是寂寞,想借幾本文學書看看,因為她是失去了自由的人,希望能把書送到東興順旅館來。裴馨園接電話的時候,恰巧蕭軍在一旁,于是他就請蕭軍走一趟,并了解一下相關情況。蕭軍接受了裴馨園的委托,帶著幾本書,以及裴馨園寫的介紹信,在一個接近黃昏的時刻,來到了東興順旅館。正是這次探望與談話,特別是讀到蕭紅攤放在小桌上的一首自己創作的名叫《偶然想起》的詩,使得蕭軍如獲至寶,“興奮得幾乎跳起來”,從而下定決心要拯救眼前這位具有迷人才華、但是懷著身孕的落魄女子跳出火海……
正是裴馨園第一個向蕭紅伸出了援手,隨后又讓同樣具有俠義心腸的蕭軍代表他前往探望慰藉,從而孕育了日后在中國左翼文壇大放異彩的雙子星座。同蕭軍不久前生活無著向多家報紙投稿以換取一日三餐的最低生活費,獨裴馨園一人伸出援手并賞識他的才華一樣,蕭紅也曾向多家媒體呼吁求救,也只有裴馨園一位報人給予了積極呼應,并且親自前往探視。于是也就有了蕭紅最終的逃出囚籠——一文不名且腆著孕肚的蕭紅,按照蕭軍之前留存的地址,自行尋到裴馨園家,裴馨園與妻子毫不嫌棄予以收留,直至蕭紅生產為止。
裴馨園為人正派,敢于針砭時弊,秉筆直書。1932年七八月間,松花江爆發百年未遇特大洪災,道外堤壩被毀,半個哈爾濱成了一片澤國。面對滿目瘡痍、大批災民露宿街頭的凄慘景象,裴馨園憤然提筆,以《鮑魚之肆》為題寫了一篇雜文,刊登在《國際協報》的副刊上。文章筆鋒犀利,矛頭直指偽滿政權的黑暗反動統治。恰巧,時任偽哈爾濱特別市市長的鮑觀澄也姓鮑。于是,惱羞成怒的偽市長竟逼令《國際協報》開除裴馨園,否則就關閉報社。社長張復生為保全《國際協報》,只得忍痛讓裴馨園先離開報社。
1932年八九月間,蕭軍的好友方未艾,從《東三省商報》調到《國際協報》,接替因抨擊時弊和偽滿黑暗統治而被解職的裴馨園,開始以“林郎”為筆名編輯副刊。方未艾是蕭軍在東北講武堂的同學,二人曾一起組織抗日義勇軍。同年10月,中共滿洲省委委員金伯陽(南滿磐石抗日游擊隊負責人之一、楊靖宇的親密戰友)和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領導成員黃吟秋,認為方未艾身居新聞輿論陣地,且進步可靠,就秘密發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后,中共滿洲省委決定在《國際協報》社建立黨的地下聯絡點。因為報社向社會各階層人士開放,既方便城里的地下組織同志來接頭聯系工作,也可以讓外鄉各抗日游擊區的同志同上級黨組織取得聯系,還不易被偽滿的特務察覺。對媒體,鷹犬們側重的是實施越來越嚴厲的新聞檢查。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報社竟會成為中共滿洲省委布局的聯絡南北滿抗日武裝的最佳聚合點。
這個由地下黨員方未艾主要負責的編輯崗位,使已經置身于我黨領導的地下反滿抗日斗爭洪流中的蕭軍,如魚得水。在方未艾等人的幫助下,蕭軍源源不斷地獲得黨領導指揮的南北滿各路抗日游擊隊英勇抗擊日寇戰斗業績的素材,最終撰寫完成堪稱“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學上的一面旗幟”的經典作品《八月的鄉村》。
而蕭紅獲得新生后邁入左翼文壇的第一篇作品,也發表在《國際協報》上。
1932年歲末,《國際協報》舉辦新年增刊征文活動,對蕭紅的創作才能已經有所了解的蕭軍和方未艾,紛紛鼓勵蕭紅也寫一篇文章,參加這次征文活動。
在大家的一再鼓勵下,蕭紅終于寫完了她的短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并由蕭軍親手交給了方未艾。經反復研究,方未艾等人認為此文主題不錯,決定予以發表。作為蕭紅《王阿嫂的死》的責編,方未艾讀后的第一感覺是:我看了認為寫得很真實,文筆流暢,感情充沛,決定發表。這樣,蕭紅以“悄吟”的筆名,正式開始了文學生涯。這年,蕭紅才21歲。方未艾回憶道:這些大都是蕭紅困頓在東興順旅社給我繪聲繪色講過的事情,雖沒有她講述時“表演”得動人,但充滿了詩情畫意。這種寫作特色,正是她后來在文壇上所顯露出的天才的表現。
在《王阿嫂的死》中,蕭紅描寫了勤勞善良的寡婦、雇工王阿嫂一家的悲慘遭遇,憤怒地控訴了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作品既來源于蕭紅幼小時對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村雇農生活的所見所聞,也同寫作時東北的大環境有關。九一八事變后,日寇侵占東北,民族的和階級的壓迫,將東北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民推向了絕境,這在蕭紅頭腦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蕭紅的這篇小說,就描寫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人民。也可以這么說,蕭紅這位曠世才女,從文學創作生涯開始,就將自己和普天下勞苦大眾的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二
與此同時,金伯陽還代表省委指示方未艾,充分利用《國際協報》的資源,盡最大可能將其打造成為反滿抗日的文藝宣傳橋頭堡。令方未艾大喜過望的是,就在他進入《國際協報》不久,便發現這里竟然是個早已存在、有著牢固根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堅強堡壘。可以說,《國際協報》是在九一八事變剛發生、中國共產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言發表后,矗立在淪陷區的一塊反滿抗日前沿陣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際協報》,也是黨內外緊密攜手、配合默契、戰斗力頗強的統一戰線陣地。
近年新發現的《國際協報》創始人張復生的簡歷、日記、論著等珍貴資料表明,該報之所以能團結一大批反滿抗日的愛國作家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為其撰寫在沉沉暗夜中透射光明的文章,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張復生是位杰出的、深懷民族大義的愛國志士。張復生的進步舉動,還曾得到我黨早期領導人和報業先驅的肯定。
1920年,《國際協報》及附出的俄文版《人民友誼報》,就積極支持中國收回中東鐵路路權。同年10月,瞿秋白赴莫斯科途經哈爾濱時,專門拜訪張復生,并在發給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的報道、評論,及后來所著的《餓鄉紀程》一書中,多次提到哈爾濱“中文報的內容都不大高明”“只有《國際協報》好些”。著名報人徐鑄成亦將《國際協報》稱為“東北最具活力的報紙”。
張復生同共產黨人的合作,早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就開始了。張復生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國際協報》率先在哈爾濱用白話文刊載新文藝作品。1923年,張復生聘請中共黨員李震瀛加入該報,專門撰寫新聞評論。《國際協報》的副刊也曾為楚圖南組織的燦星文藝社和孔羅蓀等組織的蓓蕾文藝社提供文藝專版。
在五卅運動中,因旗幟鮮明聲援群眾愛國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罪行,《國際協報》曾一再被迫“開天窗”,從而在廣大讀者中贏得了信任,發行量陡增一倍多。1928年12月29日東北易幟后,《國際協報》開始成為東北地區頗有影響力的報紙,進入發展的全盛時期。曾有日本商人想在《國際協報》發商業廣告,被張復生嚴詞拒絕:“給多少錢也不給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消息傳到哈爾濱,張復生懷著一顆熱血沸騰的愛國之心,憤然揮筆,以《日本軍隊能如此侵占東北?》為總題目,從9月22日起,逐日撰寫社評,痛斥日寇占領東北的大規模侵略行徑,謳歌馬占山將軍率部抗敵,呼吁國人破除對國際聯盟的幻想,堅決反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喪權辱國的“不抵抗”政策,響亮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唯有從屈辱警覺中堅忍奮斗”的口號,號召東北民眾團結抗日。《日本軍隊能如此侵占東北?》總計發稿50篇,有六七萬字之多,不但在東北3000萬人民中起到了鼓舞御侮士氣的作用,也讓全國同胞見證了東北人民眾志成城、同仇敵愾、不甘做奴隸的堅強決心。
張復生還派出記者趕赴沈陽現場采訪,并刊發專版揭露日本法西斯暴行。與此同時,他適時創辦《國際畫刊》,發布一系列揭露日軍暴行的新聞照片,如“日軍在沈陽街市令中國市民面墻而跪,然后用槍刺刺之”“日軍活埋看《不準逗留》布告之中國人民”“日軍在沈陽綁縛中國人街市示眾”等。《國際畫刊》初期發行3000余份,很快就超過10000份。《國際協報》的發行量水漲船高,每期增至10000多份。
在馬占山將軍“打響抗戰第一槍”——血戰江橋期間,張復生在《國際協報》上發起捐款勞軍的群眾性活動,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響應。張復生還派出多名記者赴松花江上游的嫩江大鐵橋前線采訪報道,并把數萬元捐款和勞軍物品及時送到抗日官兵手中。
1932年3月,國際聯盟派出以英國人李頓為首的調查團到東北調查,隨團的中國記者,是上海《申報》的戈公振和《新聞報》的顧執中兩位資深媒體人。調查團到達沈陽后,就被日本占領當局強行阻攔。于是,兩位記者將報道任務委托給《國際協報》的總編輯王研石。東北淪陷后,王研石是唯一與關內各大報保持報道聯系的人,他絲毫不懼日本侵略者的淫威,深入事變現場詳細考察,據實寫出了調查報告。然后,交給戈公振和顧執中兩位南方報人在關內的大小報紙上發表,揭露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以武力吞并東北的狼子野心,聲討了日軍對手無寸鐵的中國老百姓、東北軍士兵進行血腥屠殺的一系列法西斯暴行。
1932年哈爾濱淪陷前后,《國際協報》曾一度停刊。日本占領當局曾逼迫張復生出任日本人控制下的《濱江日報》董事會負責人,張復生堅辭不就,展現出一位中華愛國志士無所畏懼的錚錚鐵骨。1932年3月7日,《國際協報》復刊。張復生在報紙復刊后,采用“有聞必錄”的編排手法,客觀而又隱晦地刊載一些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抗日活動和全國各地群眾反對不抵抗政策的消息。
《國際協報》還根據英吉利-亞細亞電報通訊社的發稿,報道江西蘇區紅軍反“圍剿”的戰況,以打破偽滿當局的新聞壟斷。他們還把一些淪陷區報刊無法刊登的聲討日寇暴行及東北各地抗日武裝英勇打擊侵略者的消息與報道,源源不斷地發往《益世報》《大公報》《申報》等有影響的報紙刊登,有力地聲援了東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1932年底,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的干事姜椿芳,從俄文報紙上尋找日軍侵略活動和義勇軍抗日斗爭等新聞,并將之譯為中文,在《國際協報》發表。哈爾濱的日本領事館及偽滿漢奸,對《國際協報》的正義舉動恨之入骨。
張復生所倚重的《國際協報》總編輯王研石,也是一位抗日救國知識分子。從一開始,王研石就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民族解放和抗日救國的立場上。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對東北的侵略,還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予以持續、公開的猛烈抨擊。日寇占領哈爾濱后,兼任天津《益世報》《大公報》和上海《申報》特約記者的王研石,天天不間斷地用密電向關內報紙發送東北抗日斗爭的最新消息。日軍通過郵電檢查,發現了王研石的抗日報道活動,立馬查封了《國際協報》。1932年5月,王研石被逮捕,遭到日寇4個月的刑訊折磨。
為了營救王研石并使《國際協報》復刊,社長張復生不惜用重金賄賂日本領事館。《國際協報》復刊后,張復生不顧日本人的反對,毅然任用王研石為《國際協報》的“編輯長”,即總編輯。1933年,堅持進行抗日報道的王研石在日寇欲第二次抓捕加害前,逃離了偽滿洲國,前往天津,正式參與《益世報》的編輯工作。后因報道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的消息,王研石被國民黨反動當局強行責令停止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后,王研石轉戰武漢、重慶等地,因其持續采訪、報道有關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殺敵且屢屢獲勝的戰地新聞,被國民黨反動派囚禁了5年半,直至1944年秋才重獲自由。
三
有毫不畏懼日寇暴政的張復生和王研石這樣的熱血愛國者擔綱《國際協報》掌門人,自然也為方未艾等共產黨人爭取、團結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士和愛國抗日讀者提供了有利條件。他們以筆作刀槍,投入到反滿抗日斗爭中去,營造了東北淪陷區愛國抗日救國的氛圍,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中流砥柱。哈爾濱淪陷后,在社長張復生和總編輯王研石的支持下,《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由方未艾和左翼作家、共產黨人羅烽的妻子白朗主持,經常刊登愛國青年的文藝作品,并專為金劍嘯、羅烽和蕭軍、蕭紅等開辦《文藝周刊》。
方未艾回憶說,白朗聰明智慧、溫文爾雅,不僅是當時哈爾濱全市唯一的女編輯,也是當時東北的第一位報紙女編輯。白朗到報社后,先是負責協助方未艾,編輯每日半塊版的文藝副刊《國際公園》。僅僅過去了幾個月,白朗便熟悉了編務工作,還獨立負責編輯婦女、兒童、衛生3個周刊。由于編務出色,白朗既吸引了許多讀者,也為總編輯王研石所賞識與倚重。在方未艾赴蘇聯學習后,白朗便全面負責副刊編輯。
與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這塊反滿抗日統一戰線輿論陣地相呼應的,是1933年8月,中共地下黨員金劍嘯、羅烽等人,通過蕭軍的朋友陳華(陳華當時在偽滿洲國首都“新京”《大同報》擔任副刊編輯),在《大同報》創辦了一個文藝副刊《夜哨》,每周1期。蕭軍、羅烽等人負責在哈爾濱收集稿件,經白朗初選及稍加整理后轉寄給陳華,再經陳華編輯并發表。《夜哨》這個副刊的刊名是蕭紅所起,刊頭系金劍嘯親筆繪制:圖案的上半部是茫茫的黑夜,中間是一片大地,底部是一道道鐵絲網,充分表達了黑夜中的崗哨這一含義。
白朗以弋白等筆名,在《夜哨》發表散文和小說。她的中篇小說《叛逆的兒子》連載了11期,由蕭紅撰寫的多件作品,刊載了13期。《夜哨》前后共出刊21期,因為發表的作品內容,及其彰顯的反滿抗日立場過于鮮明,引起了日本特務機關的敵視。《夜哨》于1933年12月24日被勒令停刊。蕭紅和白朗是在《夜哨》上發表作品最多的女作者。
而在《國際協報·國際公園》和《大同報·夜哨》上經常發稿的那些熱血青年,又都成了另一個反滿抗日文藝宣傳陣地——“牽牛房”的積極參與者。
牽牛房,是黃之明(黃田)和袁時潔(袁淑奇)夫婦的家,地點在哈爾濱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一座大院內。他們的住房甚是寬敞,門窗朝南,屋內客廳、臥室、書房、廚房、衛生間一應俱全,在當時的哈爾濱較為罕有。黃之明可謂“白皮紅心”的人物——明里,他是偽哈爾濱香坊警署的一名警佐,而暗里,他則是一名活躍而又堅定的地下抗日分子。豪爽的黃之明,與蕭軍、方未艾在東北講武堂同過學,彼此感情深厚。后來,蕭紅、蕭軍被迫逃離哈爾濱南下,二蕭的盤纏以及在青島時期和上海初期的生活,都離不開黃之明的慷慨解囊。
牽牛花盛開的季節,正是地下抗日分子活動最為活躍的季節,粉白色、紅白色和紫中透白的牽牛花,爬滿了房子四周的窗戶和風斗門(房屋入口處抵御寒風的過渡門),甚是令人賞心悅目。于是,黃之明興致勃勃地提議,把這座房子命名為“牽牛房”,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響應。
當時常來牽牛房的蕭紅、蕭軍,雖是“職業作家”,但卻是牽牛房所有客人中最貧窮的一對夫婦,他們常常餓著肚子前來參加聚會。剛剛脫離苦海的蕭紅思想進步很快,她對袁時潔說:“一個女人要想翻身,必須自己站起來,參加革命事業,不給男人當‘文明棍’,不給男人當‘巴兒狗’。”這番話,展示出蕭紅率性、獨立、狂放的性格。
常來牽牛房的,還有一對在學校任教員的夫婦,男的姓孫。他們經常在客人稀少的時候來牽牛房做客,每次來時,都要交給主人幾張印著共產黨領導的“東山里抗日游擊隊”打擊日寇勝利消息的油印抗日宣傳品。袁、黃夫婦閱讀完刊有抗日隊伍勝利消息的宣傳品后,都會轉給其他人閱讀。這些宣傳品,順理成章地成為日后蕭軍創作《八月的鄉村》的基本素材的一部分。
四
蕭紅《生死場》1935年12月在上海秘密出版前,已在沉沉暗夜的東北淪陷區綻放出耀眼的光芒:該書第一節《麥場》和第二節《菜圃》,在蕭紅和蕭軍1934年6月12日逃離偽滿洲國前,已正式發表在白朗主編的《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上,時間為1934年4月20日至5月17日。這篇名為《麥場》的文字,雖然沒有直接出現反滿抗日內容,但這部作品的核心,是昔日麻木不仁、渾渾噩噩,而今覺醒了的黑土地上的農民,在中國共產黨和磐石人民革命軍的感召下,武裝起來,打擊日本侵略者和徹底推翻偽滿洲國的黑暗奴役統治。在沉沉暗夜的偽滿洲國文壇上,《麥場》的發表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同時,《麥場》也是對偽滿統治當局瘋狂迫害堅持反滿抗日立場的左翼文化人士、推行法西斯暴政的莫大諷刺。讀者通過《麥場》,見證了當時中共滿洲省委領導的反滿抗日左翼文學運動。反滿抗日的文學運動,猶如一把插入敵人心臟上的利刃,又如同一棵生長在花崗巖石縫中的小草,頑強地向外探出它不懈抗爭的腦袋。
1935年11月14日的夜里,魯迅先生在為其喜愛的女弟子所著的《生死場》撰寫的序言中,作出了入木三分、足以引領全民族抗戰的高度評價:“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
慧眼獨具的魯迅先生,引領蕭紅、蕭軍走向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與全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左翼文學運動,可謂二人投身抗戰文學、成為文壇精英和民族先鋒斗士的伯樂和導師。而1932年10月至1934年5月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里,由地下黨員方未艾及其繼任者白朗負責編輯的《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不啻孕育蕭紅、蕭軍這對耀眼雙子星座的搖籃。
(作者:秋石,系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兩個倔強的靈魂》《蕭紅與蕭軍》等)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山東服裝職業學院:數智引擎驅動職教育才“加速跑”
- 面對教育數字化“變局”與“新機”,山東服裝職業學院以“數智+”為引擎,積極探索數字化轉型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新路徑,奮力書寫新時代...[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7-25
【光明時評】“本升專”現象帶來的啟示
- “本升專”回爐教育的效果如何。從今年就業市場呈現出的新變化新特征來看,熱門領域和新興產業對人才的需求特別旺盛,傳統行業轉型對勞動者...[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7-25
青島嶗山區司法局為企業提供法律指引
- 本報訊記者曹天健通訊員卞旭前不久,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惠企法律服務團隊走進王哥莊街道,為企業員工舉辦了主題為“勞動關系法律風險防范”...[詳細]
- 法治日報 2025-07-25
去哪兒旅行上線英文版
- 本報電近日,去哪兒旅行宣布上線APP的英文版頁面,為游客提供酒店、機票、火車票、門票和度假產品的英文預訂服務。去哪兒旅行數據顯示,今...[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7-25
田園新場景帶熱文旅消費
- 近日,綿亙于山東省濟寧市東部山區的泗水縣,入選國家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試點名單。如今,每到節假日,絡繹不絕的游客來到泗水,穿梭于桃...[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7-25
為中泰合作串起更多“共贏鏈”(僑界關注)
- 一顆泰國榴蓮,從果園走上中國餐桌,離不開生長監測、數字品控、冷鏈運輸等各個環節的高效銜接;一款泰國品牌飲料,在中國市場暢銷多年,背...[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7-25
青島嶗山首批“新就業群體友好醫院”掛牌
- 本報訊7月16日,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衛生健康局聯合嶗山區委社工部聯合開展“健康護航,騎享清涼”暨新就業群體友好醫院揭牌活動,青島睛美...[詳細]
- 工人日報 2025-07-25
“這里有像媽媽一樣的老師”
- 本報訊“我和孩子媽媽是快遞員、外賣員,沒有時間管孩子,上其他培訓班要交不少的費用,在工會的托管班,既不花錢,還有人管、有玩伴,更能...[詳細]
- 工人日報 2025-07-25
從“體檢”到“復診”筑牢安全防線
- “從原料進廠到產品出廠,每個環節都有了更清晰的質量把控標準,多虧了市場監管部門的‘專家問診’,幫我們解決了多年的工藝難題”。近日,...[詳細]
- 中國市場監管報 2025-07-24
山東鄒平:延伸服務半徑 守護婦兒健康
- □山東省鄒平市黃山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賀文近日,山東省鄒平市黃山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婦保科主任呂瑩瑩來到產婦張女士家中開展上門隨訪...[詳細]
- 健康報 2025-07-24
水蜜桃喜迎采摘季 樹熟品質彰顯鮮甜風味
- “您聽過平谷有人種植水蜜桃嗎”。盛夏七月,踏進北京市平谷區山東莊鎮山東莊村的畇鵲農莊,飽滿的水蜜桃壓彎枝頭,空氣中彌漫著濃郁的桃香...[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