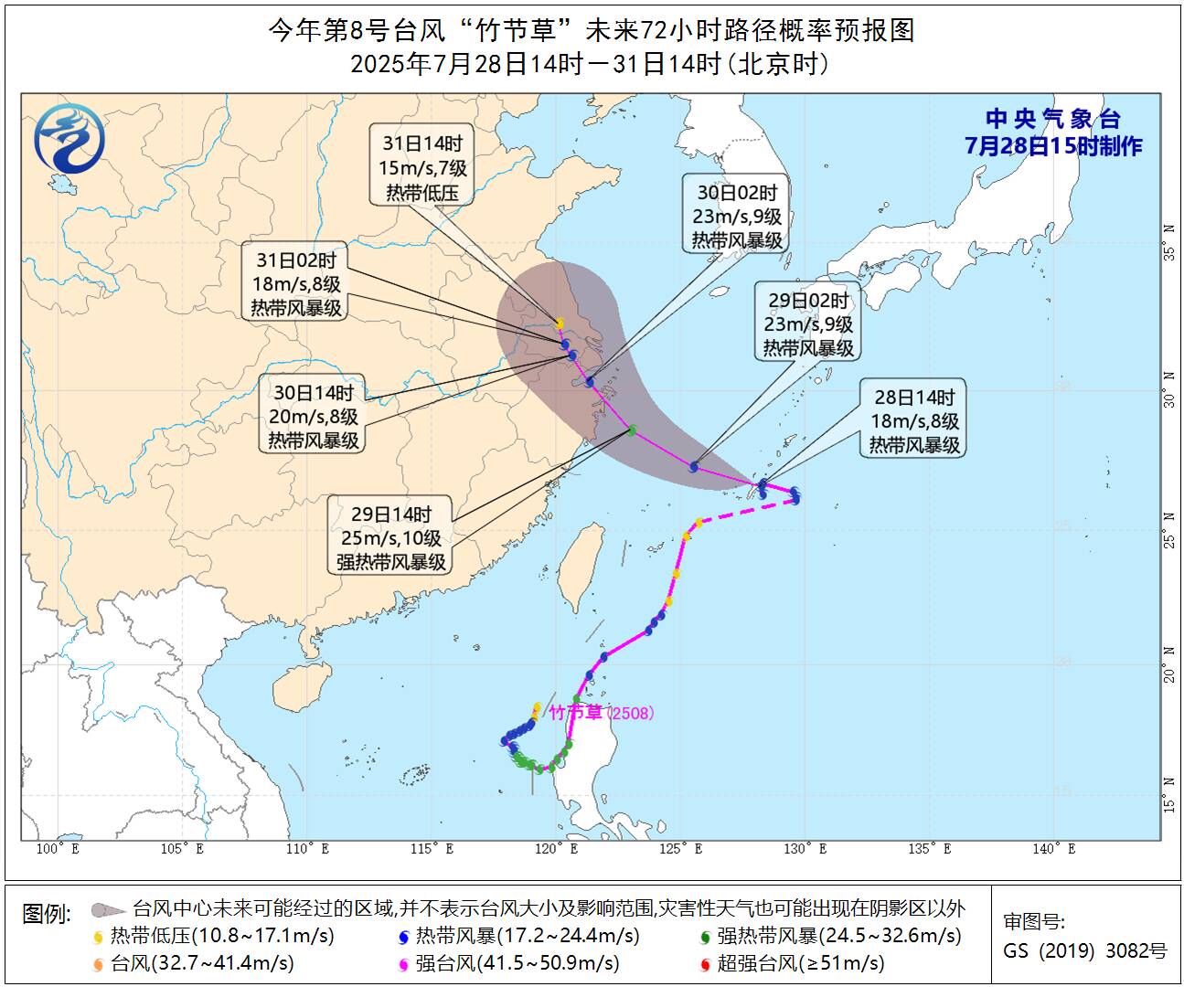漢學家見證中國“文學村莊”之變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7-31 08:49:07
原標題:漢學家見證中國“文學村莊”之變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原標題:漢學家見證中國“文學村莊”之變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來到清溪村時,池塘中荷葉田田,花朵開得正盛;花鼓戲唱腔清麗,余音不絕如縷;作家書屋敞著門,迎接四方讀者;三三兩兩的孩子走進中國當代作家簽名版圖書珍藏館,用閱讀給夏日的燠熱帶來一絲清涼……這座古老的村莊因作家周立波而聞名,又因文學走出了一條文旅融合發展之路。
7月24日至25日,由中國作協主辦的“在世界文學地圖上發現清溪——漢學家、文學翻譯家走進清溪村”活動在此舉行。來自11個國家的12位漢學家、文學翻譯家與9位湖南作家齊聚這座“文學村莊”,開啟跨越文化與時空的文學對話。
周立波故里來新客
“這個離城二十來里的丘陵鄉,四圍凈是連綿不斷的、黑洞洞的樹山和竹山,中間是一片大塅,一坦平陽,田里的泥土發黑,十分肥沃……林里和山邊,到處發散著落花、青草、朽葉和泥土的混合的、潮濕的氣味。”這是周立波筆下的清溪村。1954年末,為深入了解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實際情況,在北京工作的周立波決定回到湖南益陽老家體驗生活,并在1957年底創作完成了這部載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杰作。
《山鄉巨變》不僅在中國頗有影響,還被翻譯成多個語種在世界傳播。保加利亞漢學家思黛說:“來清溪村前,我就看過《山鄉巨變》。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本書在保加利亞就有譯本。”他認為,寫小說要關注人物的個性。周立波深諳此道,他愛筆下的人物,寫出的故事才能精彩、有趣。此外,周立波的代表作《暴風驟雨》在保加利亞也有譯本,思黛的學生近年還翻譯了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
如今,在清溪村,周立波故居被完好保存。這座已有200多年歷史的院子,是作家出生、成長、創作《山鄉巨變》的地方。“立波是作家的筆名,源于英文‘liberty’,體現了他對自由的追求和渴望。”“1942年,周立波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親耳聆聽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觀。”踏入老宅,漢學家、翻譯家們認真聆聽講解,仔細觀看一張張老照片和泛黃的手稿,了解周立波的生平和文學追求。
來自突尼斯的哈立德對周立波并不陌生。“我本科時就聆聽過老師講述周立波先生的故事,如今在突尼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我總向學生強調,這位扎根解放區的作家,和丁玲、趙樹理等一樣,是具有典型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的作家。”在他看來,周立波的價值在于讓我們明白,“文學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扎根在泥土里,和村莊一起生長。”
文學與村莊的關系在清溪村得到完美詮釋,這方水土孕育了一位著名作家,又通過作家的筆而馳名中外。如今,依托文學資源,清溪村建成了全國最大的作家書屋群落和全國首家中國當代作家簽名版圖書珍藏館,正迎接四方賓客感受新的山鄉巨變。2024年,清溪村共接待游客135.36萬人,旅游收入1700.1萬元。
作家書屋裝點“文學村莊”
王蒙清溪書屋、梁曉聲清溪書屋、遲子建清溪書屋、阿來清溪書屋、王躍文清溪書屋、劉慈欣清溪書屋……22家書屋點綴在這座飄著花香草香的村子里。記者在遲子建清溪書屋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額爾古納河右岸》等作家代表作,品類齊全,應有盡有。在裝飾上,遲子建清溪書屋突出北國雪鄉特色,在進門處用雪花和馴鹿等元素還原了作家故鄉北極村的風光。據了解,清溪書屋由普通民居改造而來,由當地村民管理,助農民增收。
在阿來清溪書屋,書架上的作品勾起了兩位漢學家的回憶。他們是來自土耳其的漢學家吉來和來自哥倫比亞的漢學家羅一人,分別翻譯過阿來的《塵埃落定》和《蘑菇圈》。二人留下寄語,感謝中國作家寫出的優秀作品,讓他們有機會將其翻譯至海外。
在清溪村,有一個地標式建筑,它的主建筑外觀酷似一排倒扣的書本,這就是中國當代作家簽名版圖書珍藏館。閑暇時,清溪村的村民和孩子們會到這里看看書,讀讀那些發生在遠方的故事。2023年2月,由中國作協發起倡議,征集中國當代作家簽名版圖書,截至目前已有7.9萬余冊入藏。
7月25日,這里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遠道而來的漢學家們跨越山海,將自己精心翻譯的作品和本國中國文學譯本捐給清溪村。白鑫捐贈了《魯迅小說選》、劉震云《一日三秋》等20部作品的阿拉伯語版;勞諾捐贈了麥家《暗算》、格非《隱身衣》等4部作品的芬蘭語版;施露捐贈了魯敏《荷爾蒙夜談》、張悅然《繭》的荷蘭語版;白蘭捐贈了老舍《茶館》等3部作品的西班牙語版……60余冊圖書將放置在“全球漢學家文學譯作清溪書架”上,被永久珍藏。
這些贈書中,有一本是1953年在布達佩斯出版的匈牙利語版《暴風驟雨》。“它不屬于我個人的翻譯成果,卻是我最想帶到清溪村的一本書。”匈牙利漢學家宗博莉·克拉拉說,這本書曾在20世紀50年代讓匈牙利讀者看到了中國農村的巨變,70多年后,它“回到”作者周立波的故鄉,“仿佛走完了從清溪出發、在異國輾轉、又回到它精神原鄉的旅程”。
讓中國文學走得更遠
鐵路橋墩上的《山鄉巨變》大幅連環畫,周立波故居里的經典作品聽書角,遍布村莊的文學金句微標語,擺放著圖書和紙筆的清吧、咖啡館,還有中國當代作家文學成就展上,由圖書封面拼成的“文學”大字墻,清溪村無處不在的文學元素給漢學家們留下深刻印象。
“這里讓我想起《詩經》里的中國,陶淵明筆下的中國。我想和陶淵明在這里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他應該會很開心。”西班牙漢學家高伯譯精通中國古典文學,翻譯過《詩經》《莊子》《山海經》等典籍,這次清溪之行讓他感慨萬千。
當現實照進文學,漢學家們對中國又多了一分了解。“在地性與世界性——從清溪文學村莊談起”座談會上,大家敞開心扉。塞爾維亞漢學家安娜動情地說:“30年前,我因為中國鄉土文學,愛上了中國的小說。讀這些書時,我感覺身處一個美麗的世界。”如今親眼看到清溪村的荷花,看到農民的勞作場景,引發了她對文學翻譯的思考。“人名、地名,地理、歷史背景不一樣,塞爾維亞讀者如何理解莫言、余華、蘇童的作品?這需要我們翻譯家精準把握和傳達作品中人的感情和經驗。”安娜說,“文學翻譯不僅是技術。”
與安娜相比,伊朗漢學家艾森的翻譯之路頗為不同。他學生時代在山東求學,研習中醫,一開始翻譯《黃帝內經·素問》《中醫脈診》等醫學著作以及《大學》《中庸》《孟子》等儒家經典。“我后來發現,要讓伊朗讀者了解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譯中國當代文學。”艾森說。他翻譯了莫言的《初戀》、路內的《慈悲》等作品,受到伊朗讀者喜愛。
和自己作品的譯者思黛在“家門口”見面,令湖南作家盛可以非常高興。“我的作品被翻譯為20個語種在海外出版,其中有思黛的杰出貢獻,他把我的作品翻譯到保加利亞。”盛可以表示,前不久,她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北妹》輸出了西班牙語版權,它寫鄉村女孩走出去后,在大城市深圳的遭遇。
另一位湖南作家鄭小驢最近也有喜事,他的《去洞庭》西班牙語譯本前幾天剛剛在秘魯利馬國際書展亮相。“是漢學家和翻譯家們,在語言的巴別塔之間,為我們搭建了溝通的橋梁。”鄭小驢說。迄今為止,他的作品被翻譯為西班牙語、日語、捷克語等語種。“今天的中國新生代作家,心態發生了很大改變,寫作也經歷了巨變。希望漢學家們從藝術審美的角度重新認識當代作家的寫作,讓我們被更廣闊的世界看見。”
即將奔赴下一站,白鑫的一段話道出了漢學家們的共同心聲,“我們留給清溪村的譯作不僅是作品,更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31省區市明確下半年穩經濟三大著力點
- 截至目前,31個省區市發布了上半年經濟“成績單”。伴隨“半年報”發布,近期各地密集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聚焦擴大內需、發展新質生產力、...[詳細]
- 經濟參考報 2025-07-31
點“數”成金,數字經濟加速跑(“十四五”,我們見證這些“第一”②)
- 中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2024年達到10.4%,首次突破10%——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了這樣一組數據。在重慶,長安汽...[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7-31
為新就業群體帶去盛夏中的清涼
- 7月以來,我國有152個國家級氣象站觀測氣溫超過40℃,未來高溫仍將持續,部分地區持續天數和極值可能突破歷史同期。不只是趙師傅,快遞員、...[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7-31
讓公平正義體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
- ??公正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一環;法官,是公平正義的裁量者與實踐者。面對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更高期待,人民法官積極履行職責,以...[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7-31
山東:健全臨災預警“叫應”機制
- 針對防汛關鍵期,山東要求全省上下立足防大汛、搶大險、救大災,細化落實各項防汛措施,快速、及時、準確發布預警信息,健全臨災預警“叫應...[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7-31
【文化評析】 樂看暑期檔電影百花齊放
- ??據數據統計,截至7月27日11時19分,我國2025年電影暑期檔總票房破50億元,檔期總人次1.29億,單日票房連續十天破億元,市場熱度顯著回...[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7-31
大阪世博會中國館參觀人數突破100萬
- 新華社大阪7月30日電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會中國館30日迎來第100萬名參觀者。??當天下午,中國館第100萬名參觀者——來自大阪的淺川輝和及...[詳細]
- 光明日報 2025-07-31
以文塑旅 加快推動文旅新業態
- 近日,山東省濟南市鋼城區政協組織委員先后到萊鋼展館、萊蕪戰役指揮所舊址紀念館等處,以“挖掘本地文化資源打造文旅產業新業態”為主題,...[詳細]
- 人民政協報 2025-07-31
補貼新政將助力失能家庭“減負增能”(聚焦?觀察)
- 民政部與財政部近日聯合印發《關于實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發放養老服務消費補貼項目的通知》,這是我國首次建立針對失能老年群體的專項服...[詳細]
- 人民政協報 2025-07-31
讓英雄的故事代代相傳(銘記歷史 緬懷先烈)
- 盛夏的北京延慶草木蔥蘢,海陀山下、媯水河畔,平北抗日戰爭烈士紀念碑肅穆矗立。近日,記者與延慶區政協委員、平北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吳晨...[詳細]
- 人民政協報 2025-07-31
喀麥隆可可,藏著“財富密碼”(國際視點)
- 地處西非的喀麥隆是全球第四大可可出口國。可可果內藏香醇的可可豆,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根據喀麥隆國家可可與咖啡辦公室的目標,喀麥隆將...[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7-31
圖書館“超長待機”,激活了什么(四海聽音)
- 夜幕落下,圖書館依然燈火通明。讓群眾走進圖書館,靠的是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升級。安徽合肥市中心圖書館通過升級空調系統,實現分區溫控,讀...[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7-31
讓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山河顯影)
- 為解除“南進”的后顧之憂,從1940年下半年起,日軍加強了對中國敵后根據地的“掃蕩”,又進行了“清鄉”“蠶食”“治安強化運動”等進攻。...[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