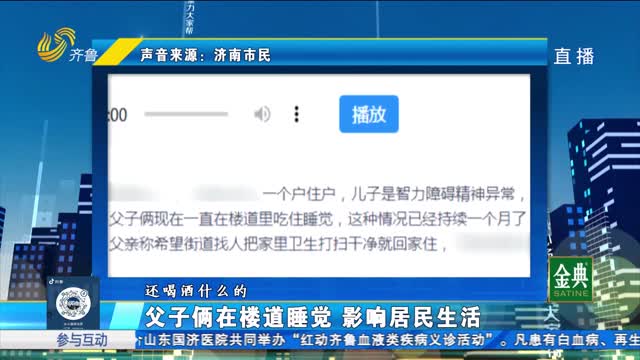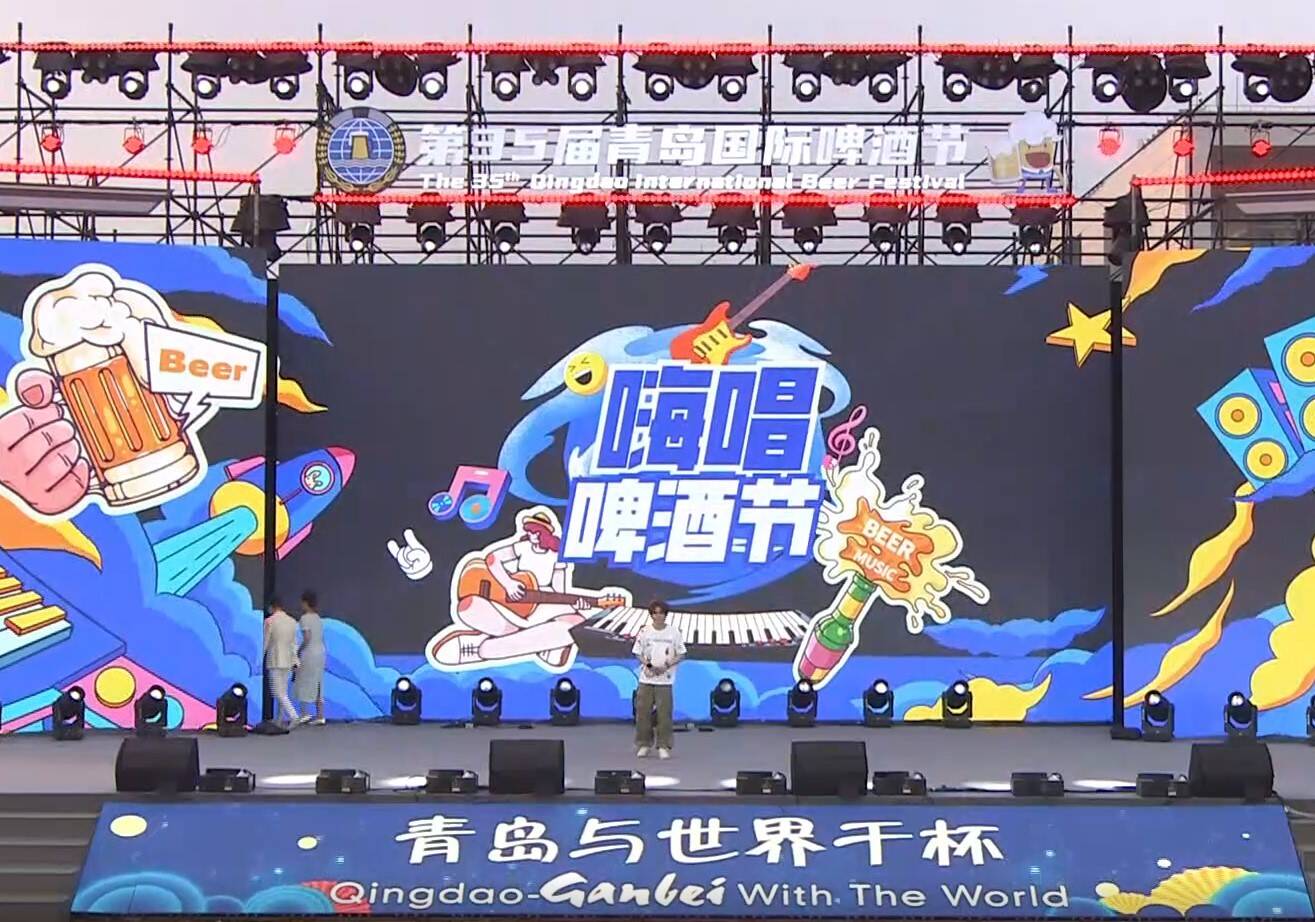河朔之風(fēng) 詩歌之路
來源:中國文化報
2025-07-22 08:30:07
原標(biāo)題:河朔之風(fēng) 詩歌之路
來源:中國文化報
原標(biāo)題:河朔之風(fēng) 詩歌之路
來源:中國文化報
馬吉照
河北,南接中原、齊魯,很早就在中華文明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北鄰邊塞,處在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沖突角力、融合共存的前沿,演繹了無數(shù)蒼涼豪放、蕩氣回腸的慷慨悲歌。當(dāng)王朝政權(quán)定都北京后,河北由邊地一躍成為腹心,又多出一份屬于大國京畿的開闊大氣、富貴雍容。無論壯游邊塞,還是入京朝圣,河北始終是時代的大手為詩人準(zhǔn)備的一個出路和選項。于是,河朔之風(fēng)雖然剛健、蒼涼,但向來不缺少詩歌的潤澤。歷朝歷代,總有本土或客籍的詩人北上南下,把繁忙的商路驛路、荒涼的邊關(guān)塞道,都變成星輝斑斕的詩歌之路。
太行山和燕山,如同一撇一捺,在燕趙大地畫出一個巨大的“人”字,無論在現(xiàn)實的地理空間里,還是在古典詩詞的版圖上,都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地位。
太行山古稱“天下之脊”(《括地志》),東漢至隋唐間,八百里太行隔開了人們普遍印象中的“山西”與“山東”。溝通山脈兩側(cè)的“太行八陘”,自然少不了詩人的身影:高適在封丘尉任上送兵到青夷軍(今張家口懷來),自幽州(今北京)出居庸關(guān),走的是最北面的軍都陘;岑參游河北,曾取道井陘(《題井陘雙谿李道士所居》)……
太行山東麓的南北大道,不僅是一條引人關(guān)注的“河朔唐詩之路”,而且為古代詩壇輸送了大量優(yōu)秀詩人,比如“初唐四杰”中的盧照鄰,“文章四友”中的李嶠、蘇味道,盛唐名家李頎、崔護,“中興高流”李嘉祐和“大歷十才子”中的李端、崔峒、郎士元、司空曙,“韓孟詩派”的重要成員賈島、盧仝,名相兼詩人李德裕,等等。許多河北本土詩人為家鄉(xiāng)留下了豐富的詩篇:有人記錄河北平原的典型景觀特點,如初唐崔湜的“回首覽燕趙,春生兩河間,曠然萬里馀,際海不見山”(《冀北春望》);有人刻畫燕姬趙女的絕代芳華、河朔健兒的精神風(fēng)貌,如西漢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北方有佳人》),中唐李嘉祐的“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住滹沱河”(《少年行》);還有漂泊游子表達(dá)對家鄉(xiāng)的深深眷念,如晚唐李德裕的“北指邯鄲道,應(yīng)無歸去期”(《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
作為與太行山攜手的另一條偉岸臂膀,燕山山脈堪稱歷代中原王朝的一道天然屏障,分隔開農(nóng)耕與游牧兩大文明類型。自今北京沿燕山南麓通往渤海之濱的榆關(guān)道,是古代詩人走向東北邊塞的首選線路。唐前的古詩寫到這一線的地名、風(fēng)物,大多出于想象,如曹植的“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艷歌行》),沈約的“迎行雨于高唐,送歸鴻于碣石”(《臨春風(fēng)》),作者本人并不需要親自來過。到了唐代,詩人普遍可以在現(xiàn)實中走得更遠(yuǎn),而這大概也是唐朝強盛、唐詩繁榮的一項重要表征。唐人取此道深入邊塞的杰出代表是高適。“摐金伐鼓下榆關(guān),旌旆逶迤碣石間”(《燕歌行》),高適漫游河朔途中所作諸篇,無疑是盛唐邊塞詩中極富代表意義的創(chuàng)作。唐代以后,遼、金、清諸朝均起家東北,從皇室到廷臣,常需往來于京師與東北之間。明清兩朝派往朝鮮的使臣和朝鮮來華的使臣經(jīng)行河北境內(nèi),通常也是走這條最為便利的榆關(guān)道。以上幾類人物,沿途所作精彩詩詞不勝枚舉,假如只拈出一首作為代表,可推納蘭性德那首膾炙人口的《長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guān)那畔行,夜深千帳燈……”
假如把詩人的行跡和詩篇比作燈火,那么,從夜空俯瞰河北,上述“太行山—燕山”一線的“人”字形詩路,就像是一條燈火通明的主街道。但整片區(qū)域內(nèi)熠熠生輝的,顯然并非只是兩條線,而是一張巨大的網(wǎng)。在太行山以東數(shù)百公里外,南北縱貫河北平原的是另一條“水上詩路”,其光輝在明清時期甚至超越了“太行山—燕山”詩路,那就是京杭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是水路交通的大動脈,毫無疑問也是詩歌之河、文學(xué)之河。南方才子進京趕考、考中后出京做官,商人到北方做生意,誰沒有坐過運河里的航船呢?而在“從前慢”的運河舟中以及沿途水驛、市鎮(zhèn)作詩,注定是古代文人的日常。
除此之外,邯鄲東南的鄴城(今邯鄲臨漳),是曹魏至北齊的六朝古都,漢末建安年間著名的“三曹”“七子”文學(xué)活動的中心,北齊時又聚集過“北地三才”和盧思道、楊衒之等河朔名家。時間進入盛唐,醉醺醺的李白騎著白馬來到邯鄲,寫下“醉騎白花馬,西走邯鄲城”(《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的詩句;年少輕狂時的杜甫,也曾“放蕩齊趙間”“春歌叢臺上”(《壯游》)。邯鄲北面的邢臺,古稱邢州,傳說是俠士豫讓行刺趙襄子之地,清初詞人陳維崧來此的前一天,剛剛涉過燕丹送別荊軻的易水,鏗鏘低回地唱出“殘酒憶荊高,燕趙悲歌事未消。憶昨車聲寒易水,今朝,慷慨還過豫讓橋”(《南鄉(xiāng)子·邢州道上作》)。石家莊北面的寶藏小城正定,古稱真定、鎮(zhèn)州,唐后期是與中央分庭抗禮的“河朔三鎮(zhèn)”中成德藩鎮(zhèn)的駐地,韓愈奉使至此,有《鎮(zhèn)州路上謹(jǐn)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鎮(zhèn)州初歸》等詩存世。正定往北,過了蘇軾做過刺史的定州,就來到寒冽透骨的易水。這是一條河北人的精神之河,一闋“風(fēng)蕭蕭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反復(fù)回響兩千年,始終不曾消歇。初唐駱賓王在此寫下名篇《于易水送人》,金元時期的元好問、汪元量、楊維楨,明清的李東陽、李攀龍、王世貞、屠隆、王士禛等名家也都留有詩作。
山河、古道,既是大地的自然紋理,也是河北人的精神紋理,它們縱橫交錯,像一張大網(wǎng),串聯(lián)起大小都邑、風(fēng)景名勝,吸引著歷代詩人行吟的腳步,也為今人的尋詩之旅提供線索和指引。河北之美,不只在風(fēng)景,也在于隨處一落腳就可能踩到的詩人足跡。在這片環(huán)抱京津、懷瑾握瑜的詩意大地上,讀詩看景,走走停停,發(fā)現(xiàn)腳下的山河與紙上的景觀可以互證不虛。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山東威海:邊旅游邊閱讀
- 本報記者蘇銳通訊員高孟峰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發(fā)展改革委、財政部發(fā)布的《關(guān)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wù)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意見》提出,“創(chuàng)新打造一批融合...[詳細(xì)]
- 中國文化報 2025-07-22
未婚女子“被結(jié)婚”8年引關(guān)注
-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周韻曦今年4月,欲辦理個人所得稅退稅業(yè)務(wù)的羅女士,在婚姻情況一欄填入“無配偶”并提交后,頁面竟彈出提示 經(jīng)與有...[詳細(xì)]
- 中國婦女報 2025-07-22
《聯(lián)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與中國性別統(tǒng)計的發(fā)展 》
- 作者 蔣永萍性別統(tǒng)計是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發(fā)展完善提高婦女地位國家機制的基礎(chǔ)和重要內(nèi)容,也是衡量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以來進...[詳細(xì)]
- 中國婦女報 2025-07-22
當(dāng)心“沉默中暑”,遠(yuǎn)離熱射病
- ●先兆中暑、輕癥中暑可讓身體出現(xiàn)明顯不適,比如口渴多汗、乏力心慌、頭暈頭痛、面色潮紅,對癥處理后便可緩解。●身體對“熱”的感覺不僅...[詳細(xì)]
- 中國婦女報 2025-07-22
27分48秒68!萬米紀(jì)錄背后的00后跑者王文杰
- 德國當(dāng)?shù)貢r間7月21日,萊茵-魯爾世界大學(xué)生運動會田徑比賽將在波鴻洛爾海德體育場開賽,奧運選手、洲際錦標(biāo)賽冠軍云集。中國長跑選手王文杰...[詳細(xì)]
- 中國青年報 2025-07-22
中超賽場打響“文明保衛(wèi)戰(zhàn)”
- 重拳打擊足球流氓,以法律為武器切割球場毒瘤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7月21日上午,中國足球職業(yè)聯(lián)賽聯(lián)合會在官網(wǎng)及多個社交平臺公布對本輪中...[詳細(xì)]
- 中國青年報 2025-07-22
2024年全國現(xiàn)有海水淡化工程158個
- 本報北京7月21日電自然資源部海洋戰(zhàn)略規(guī)劃與經(jīng)濟司近日發(fā)布《2024年全國海水利用報告》。報告顯示,2024年全國現(xiàn)有海水淡化工程158個,工程...[詳細(xì)]
- 人民日報 2025-07-22
水利部向14省份發(fā)出“一省一單”靶向預(yù)警
- 本報北京7月21日電記者從水利部獲悉 7月20日8時至21日8時,受臺風(fēng)“韋帕”影響,廣東沿海、海南大部、廣西東南部、浙江南部、福建沿海等地...[詳細(xì)]
- 人民日報 2025-07-22
首批“好房子”建設(shè)經(jīng)驗做法發(fā)布
- 本報北京7月21日電為加大“好房子”工作推動力度,住房城鄉(xiāng)建設(shè)部近日發(fā)布《“好房子”建設(shè)經(jīng)驗做法》,涵蓋了出臺推動政策、加強技術(shù)支撐...[詳細(xì)]
- 人民日報 2025-07-22
上半年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消費增長14.6%
- 1—6月,全國網(wǎng)上零售額增長8.5%。其中,品質(zhì)商品、以舊換新、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消費增長較快,重點監(jiān)測平臺的數(shù)字產(chǎn)品、15類國補家電和數(shù)碼產(chǎn)品、網(wǎng)...[詳細(xì)]
- 人民日報 2025-07-22
世界首份月球鎂環(huán)樣品礦物學(xué)檢測報告發(fā)布
- 科技日報訊近日,世界首份月球背面鎂環(huán)樣品礦物學(xué)檢測報告在山東大學(xué)發(fā)布。這項成果聚焦月球南極—艾肯盆地中一個名為“富鎂輝石環(huán)”的特殊...[詳細(xì)]
- 科技日報 2025-07-22
1月至6月全國網(wǎng)上零售額增長8.5%
- 本報北京7月21日電記者董蓓從商務(wù)部獲悉,1月至6月,擴消費政策在電商領(lǐng)域落地見效。數(shù)據(jù)顯示,1至6月全國網(wǎng)上零售額增長8.5%。品質(zhì)商品、...[詳細(xì)]
- 光明日報 2025-07-22
構(gòu)建啤酒經(jīng)濟文化生態(tài)圈,國際啤酒節(jié)聯(lián)盟合作機制2025青島會議舉行
- 7月19日上午,國際啤酒節(jié)聯(lián)盟合作機制2025青島會議在金沙灘啤酒城舉行。多位國際啤酒節(jié)代表和專家學(xué)者圍繞“如何提升啤酒節(jié)經(jīng)濟社會效益”...[詳細(xì)]
- 中國日報網(wǎng) 2025-07-21